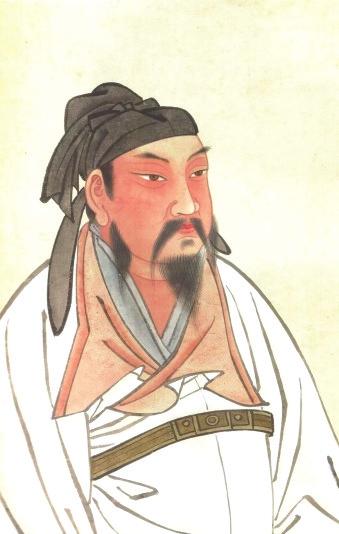李白被贬遇赦,无穷快意出心中
李白像(马睿临)
在重庆市奉节县瞿塘峡拍摄的猴子。新华社资料图片
长江三峡巫峡段景色。新华社资料图片
长江瞿塘峡风光。新华社资料图片
□马睿(下)
李白遇赦乘舟东下的三峡航道素以水急滩险而著称,“蜀江号天下之至险,与其他水路大不相侔。瞿塘、滟滪及诸恶滩密如竹节”(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卷四《再论马纲状》)。为适应这种暗礁林立、险滩密布的航道,蜀船大多设计成平底型,船两侧都造成鼓突的外形,借以增加船体的稳固性,故而“下峡舟船腹似鱼”(元稹《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蜀船“腹圆而首尾尖狭,所以辟滩浪”(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九《舟车》)。这种科学的设计,使得往来于三峡的蜀船具有速度快、阻力小、重量轻、载荷大、方向灵活等多种优点。直到清末民初,三峡上的“麻秧子”船,仍然延续了这种设计。
航道狭窄 三峡险峻水流湍急
在设计上,蜀船的船头、船尾各有一艄,以增加船夫对航行方向的控制力。此外,船上还设置了独特的戙(dòng),这是一种硬木长竿,竿头有横木,其作用在于支撑外物,防止船体触碰礁石岸石。当风力不足时,峡船还需用人力牵引,为此,船上配备了一种叫作“百丈”的纤绳。这种纤绳坚实耐磨,可以在岸石上长期拉引。用于划水的船具还有桨、桡、艣(lǔ)等,这一系列先进的船具,有效地保障了航行安全(王周《志峡船具诗序》)。
蜀船上所用风帆也比其他船只大得多,“舟船之盛……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大型风帆可以提高对风力的利用率,提升航速。另外,蜀船不仅采用了先进的钉接榫合工艺,而且船底不是用铁钉,是“以柘木为钉,盖其江多石,不可用铁钉”,又称“艬(chán)船”(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藤船》)。由于航道狭窄险峻,三峡船工多为世代以此为业者,驾船技术十分娴熟、高超。据史料记载:“蜀之三峡……皆险绝之所,自有本处人为蒿工,大抵峡路峻急,故曰:‘朝发白帝,暮彻江陵’”(李肇《唐国史补》)。
川江行船,旧例是中夜停泊,破晓开船(杜甫《放船》)。李白是早上启程的,瞿塘峡的风速以午后最大,夜间次之,早晨、傍晚较低,并有随高度增大的规律。瞿塘峡的航道十分狭窄,“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岸间,阔狭容一苇”(白居易《初入峡有感》)。三峡的河床坡度也比较大,平均每5公里就要下降1米。加之此时正值长江一年一度的“桃花汛”,江水猛涨,平均流速可达到10公里/小时,急流险滩处甚至可达16-25公里/小时。波涛汹涌的江水,从弯转曲折的峡谷中夺路而出,一泻千里,东流而下。
船体轻、船技高、风力足、航道窄、汛情大、水流急,加之又是顺水行舟,只需要稍稍再划一划桨,“千里江陵一日还”自然易如反掌!
水清山秀 三峡猿猴自古有记载
那么,李白为什么先要到江陵,而不是一口气直接回浔阳呢?其实,这与长江的航行条件有关。长江上游与下游的航道条件差别很大。吴船的船型宽大、船体扁平、方头方艄、平底,抗风性好、载重量多,但航行阻力大,操作不灵活,速度也慢。适宜在风大、流缓、江面宽阔的长江下游航行,却无法在滩多水急的三峡航行。所以,蜀船所搭载的货物,往往需在江陵(今湖北荆州)换装吴船,再运往下游。从江南上运的货物,也需在江陵改由蜀船运往成都。因此,江陵就成为长江中游的一处航运中转站。不仅进出巴蜀的货物要在江陵换船,往来的行旅客商也是“风雨荆州二月天,问人初雇峡中船”(窦群《自京将赴黔南》)。作为商业枢纽,“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时人称云: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六六《轻薄二》之“卢程”条)。作为最爱热闹之人,李白自然也要在江陵停留一下,再换乘吴船东下。
由于独特的地质条件,三峡两岸的农业并不发达,因此森林资源保存较好。茂密的森林使这里水清山秀,飞鸟游鱼,虎啸猿啼,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唐时的长江水质十分清澈,人们常把三峡水称之为“桃花水”“绿水”或者“渌江”,如:“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刘禹锡《竹枝词》),“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张说《下江向夔州》)。另外,当地丰富的森林植被,也可从唐诗中得到反映,如:“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巫山枕障画高丘,白帝城边树色秋”(《巫山枕障》)。
良好的森林资源,为野生动物的栖息和繁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历史上,三峡一带曾广泛分布有华南虎、犀牛、大熊猫、鹿等多种动物,而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动物,则非猿猴莫属了。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对三峡猿猴的记载。“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屈原《九歌·山鬼》)是表现猿猴夜鸣的声音,“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淮南小山《招隐士》)是描写猿猴灵敏矫捷的动作。到了唐代,描写猿猴的文学作品就更加丰富了,如:“我来凡几宿,无夕不闻猿”(孟浩然《入峡寄弟》),“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孤石隐如马,高萝垂饮猿”(杜甫《荆门浮舟望蜀江》)。
心情畅快 提笔写就三唐“压卷之作”
1988年秋,古生物学家黄万波在对“巫山人”遗址进行发掘时,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在海拔1100米的太平村大脚洞发现了一颗长臂猿下牙床。据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和艺术史实验室鉴定:该化石距今仅200年,这表明直到清朝晚期,三峡地区都还有长臂猿生息繁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人还曾在三峡宜昌段的牛肝马肺峡目睹过猴群(《北京晚报》1984年9月29日第七版)。长臂猿善于鸣叫又具有呼应齐鸣的习性。其喉部具有囊状物与喉头腔相通,作用有如鸣囊,用以扩大叫声。通常由10只左右的个体,组成类似家族式的小群。每日清晨常作集体大声鸣叫,音调清晰,高昂而响亮,震动山谷(瞿明刚《论长江三峡的啼猿意象》,《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2期)。季春三月,正好是长臂猿的发情期和交配期,它们彼此首先互相接近,求偶声变得更为响亮,声音较长而有曲调。经多次试情接触,选定配偶,最后进行交配。在三峡,猿声在山谷回声的作用下,显得更加响亮、悠长。
当年初遇大赦的李白,心情一定非常舒畅,即使历来让人闻之断肠的猿声,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万丈豪情。这首诗是李白七言绝句中的代表作,后人推崇备至,被誉为三唐“压卷之作”。绝大多数人在初读此诗时,都会感觉到一个“快”字。全诗无一字写“快”,但读之字字觉“快”!全诗无一句写“喜”,吟之却句句生“喜”。的确,蜀船的航速太快了,两岸猿声犹在耳畔,轻舟已达江陵矣!但更重要的是李白的心情畅快。
自永王兵败(757年二月)以来,李白先后经历了被捕入狱、搭救出狱、入幕宋军、上书迁都、再次入狱、长流夜郎、遇赦放还。短时间内的大起大落,完全让李白晕头转向,狼狈不堪。当遇赦东下,即将与家人团聚、骨肉重逢,甚至东山再起,亦未可知。焉不酣畅淋漓!如此痛快,又岂能无诗。于是,李白提笔一挥,三唐“压卷之作”成矣!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