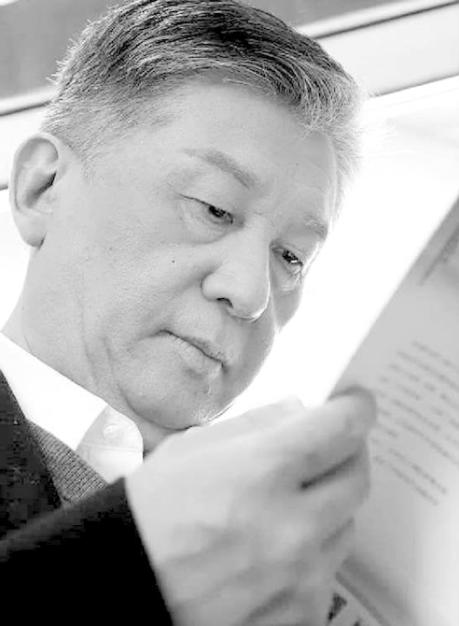从跨越30年对话录深入了解孙甘露
上海作家孙甘露
《被折叠的时间:孙甘露对话录》
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体中,孙甘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1985年,26岁的邮递员孙甘露在上海作协举办的青年作家讲习班学习后,写出小说《访问梦境》,后在《上海文学》发表,自此走上文学之路。之后他写出《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一系列富有语言实验性的作品。
孙甘露的作品被不少评论者归入了“先锋小说”“探索(实验)小说”。毕飞宇曾说,“在先锋文学的层面,余华、苏童和格非在社会层面影响最大,但走得最远的是孙甘露和残雪。”
2022年,沉潜多年的孙甘露推出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这部作品表现出与他此前作品迥异的面目:故事性非常强,带着悬疑、谍战色彩。《千里江山图》的主要背景和情节发生在上海,它既是一部革命史,也是一本风物志。原著通过叙事回溯时代风貌,通过街巷、饮食、视觉和味觉唤起人们对上海的记忆,通过浙江大戏院、世界大旅社、四马路菜市场、格致公学和金利源码头等城市地标搭建起老上海的“舞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故事发生在1933年的上海,那一年,茅盾先生在上海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允许我借此向这位前辈作家表示敬意吧。”孙甘露感慨,“上海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我们有幸在这里生活、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犒赏了。”
2023年10月,孙甘露因《千里江山图》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成为继王安忆、金宇澄之后,第三位获得茅奖的上海作家。
在这些作品背后,孙甘露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2024年3月,一本收录孙甘露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与多位友人三十多次对话录的作品——《被折叠的时间:孙甘露对话录》,由译林出版社推出。
书中对话时间跨越三十余年:自1993年开始,集中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对谈对象既有毛尖等学者,也有小白、王朔等作家,此外还有徐静蕾等电影人,谈话的主题既涉及上海、小说、写作等与作者相关的内容,也涉及当时流行的电影、文学风尚的变化等时代元素。在对谈中,孙甘露细数对自己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和电影,回溯自己的写作来路和初心。例如在与罗岗教授的对谈中孙甘露提到,“作家就是要把内心的语言翻译出来。”在另外几场访谈中,他提到,“小说的本质是虚构,而非所谓故事”“无论怎么变,文学的功能仍在人心”等。那时文学方兴未艾,纸媒尚且兴盛,电影票房过亿已属罕见,一切都在生长。三十余场对话,以问答的形式,记录下文学黄金时代的气象与细节,以及其间写作者的认知与感悟。
有关孙甘露,王朔的一句话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化研究学者汪民安专门写过一篇文化批评《孙甘露:汉语中的陌生人》(被收入《被折叠的时间:孙甘露对话录》作为序言),来深入剖析孙甘露的写作造诣。
在文中,汪民安提到,“孙甘露是没有写作程序的人,他不知道下一个词语会从哪里召唤而来,更不知道下一个句子会出现怎样的节奏、面貌、气息。他的写作就是写句子,就是要创造出一些前所未有的句子,每一个句子都是一个发明,每一个句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句子如此考究,考究得令人惊讶,它们看上去都像是汉语中的陌生句子,好像不是汉语写出来的句子。这些考究的词语组合、考究的句子如此之频繁,一个连接一个——或许,在当代作家中,没有谁的写作比孙甘露更加消耗体力了。一个作家总是能够写出令自己和读者感到陌生的句子,这是文学的伟大至福。”
从表面来看,孙甘露算是写作数量最少的作家之一。在收入《被折叠的时间:孙甘露对话录》中的“孙甘露VS木叶”对话中,孙甘露自己也说,“我希望落伍一点、慢一点、少一点。”
但在汪民安看来,“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素质,就是写出属于他的句子,写出不能被别人模仿的句子,写出即使将他的名字抹掉但仍能够被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的句子,写出让他的民族语言感到无比愕然的句子——孙甘露当之无愧地属于这类少数作家。在这个意义上,他非常多产。”
在文章最后,汪民安写道:“在当代的作家中,孙甘露或许是最为缓慢的。他的小说流淌着溪流一般的忧伤。时光催人老去,唯有藏身于语词的深邃之处才能获得永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图片由译林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