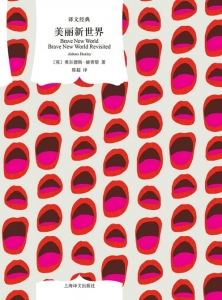从赫胥黎到莫言再到80后科幻作家
笔下“代孕”都有无法直视的隐痛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莫言的《蛙》。
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
近几日娱乐圈的热点事件,让“代孕”这个词成为一个出圈的顶流热词。这个词涉及到医学技术、道德底线、生命伦理与科技之间的矛盾冲突等复杂因素,引发人们的思考。
其实,在文学写作领域,它很早就成为中外作家,尤其是科幻作家探讨、书写的重要话题。比如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莫言的《蛙》、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等。
《美丽新世界》和《蛙》中外文学早就涉及“代孕”
在1931年代出版的《美丽新世界》中,作者赫胥黎提出了“人造子宫”的设想,在人类社会的26世纪,基因技术高度发达,生孩子的事情完全由生命工厂负责。在一条条生命流水线上,首先进行基因设计,然后是克隆,最后小孩在人造子宫中发育成长。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言:大多数人并不真正想要自由,因为自由包含责任,大多数人害怕责任。
无独有偶。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早涉及“代孕”话题的是得到鲁迅提携的左翼作家柔石。在创作于1930年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中,柔石描写了母亲“春宝娘”勤劳、朴实、善良的故事。但为了丈夫和儿子的生存,她忍辱负重,去作地主传宗接代的工具。这是一幕关于女性的悲剧,春娘被蹂躏、被压迫、被摧残,被强制一次次地与亲生骨肉分离。柔石用其冷峻的笔触、深切的情感,展现了对底层人民的同情。
首次发表于1985年的《使女的故事》,近些年来因为改编为影视剧集,成为大火的科幻作品。故事发生在近未来的美国。核战争爆发让环境遭到严重污染,人口出生率急剧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端组织趁势崛起,在美国发动政变,建立了基列共和国。在这个国家,少数拥有生育能力的女人被统一管理。所有人的最高使命都是:生育。《使女的故事》作为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整体氛围压抑、荒诞。
2009年,莫言的《蛙》出版。其中也出现了“代孕”情节。主人公万小跑和不孕妻子小狮
子,年过五旬仍然很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可此时的他们已经难以达成这个愿望。后来,小狮子找到陈眉帮忙“代孕”。陈眉本来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后来遭遇大火不幸毁容。陈眉处于心理和身体极度悲伤虚弱的状况中,一度想以死了结,但她一想到父亲在医院的欠款就无法安然离开,走投无路的陈眉答应了小狮子。怀孕期间,陈眉对这个孩子产生了母爱的共鸣。后来,她跑到万小跑为孩子举办的喜宴上去抢孩子,救子心切的她,抱起孩子就开始暴走。
科幻作家的超前思考 代孕面临情感和伦理困境
相比其他类型文学,在科幻文学领域,代孕是最容易被触及的话题。多届华语科幻星云奖评委、科幻博士张凡对科幻文学有较为深入的专业研究。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他首先提到,“创造生命形态和改变生命形态,一直是科幻小说史上较为常见的主题。近几年,更是发展出更多的内容。以前没有技术模型,只是单纯设想。现在则有资本和社会的考虑。”张凡梳理举例说,“在某种意义上,最早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都算是代孕小说,只不过是人类孕育怪物。近期比较火的有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其实《异形》也是代孕,只不过是外星人找人类代孕。”
在国内当下科幻文学界,“代孕”也被作家们拿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张凡提到国内著名的科幻作家陈楸帆的短篇科幻小说《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在这部比较试验性的剧本形态的小说中,陈楸帆用极富张力的故事和语言讲述了代孕所面临的情感纠结和伦理困境。
有读者读到这篇小说感到“很震撼”,“一旦涉及情感伦理层面,太多问题无解、无奈、无力。”
张凡赞赏这部小说“力求形式革命,将小说、影视、艺术、科技混搭,渴望突破科幻的维度,引领新的科幻浪潮。《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用纪录片视角进行了量子纠缠,完美处理好镜头视角和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具有批判深度和悲悯情怀。”
在张凡看来,陈楸帆比较敏感,抓住了“代孕”这个主题进行艺术表现,“除了偏于想象的很遥远的远景科幻小说,其实现在很多科幻小说,是一种现实主义描写。”
对于像“代孕”这样比较有争议的话题,作为科幻创作者,在创作相关作品时该如何处理好这个争议的问题,张凡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社会上的争议主要是在资本、人性和伦理上。作为科幻创作者,可能会更加关注科学技术和未来对现实社会的入侵,所引起的对人类整体的冲击,把自己的超前思考写出来,对社会是一种有效反馈。”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实习生李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