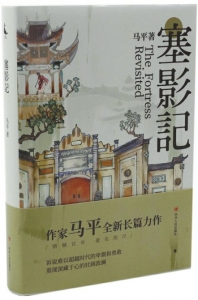“诗人小说家”马平:话语恰切,诗意自生
马平
《塞影记》
《高腔》
从一个乡村人物的历史,书写中国百年沧桑巨变的历史。书写民族寓言、家族史诗,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领域内,一直有着悠久的传统。
四川作家马平的《塞影记》被视为是这个绵延群山的又一座不容忽视的山峰。《塞影记》以四川武胜县宝箴塞为原型,通过一位平凡的百岁老人雷高汉与鸿祯塞羁绊一生的经历,带出了巴蜀乡村百年的风云变幻,呈现了那一方水土的情深义重。
作品曾在《作家》杂志2021年第一期首发,随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国内多位评论家都给予《塞影记》很高的评价。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特别适合改编为影视剧。据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王其进介绍,《塞影记》一书出版后,受到许多影视公司的关注,出版社正与各方积极洽谈。
8月1日,盛夏正隆,万物闪光。封面新闻记者与马平进行了一番深入的对话。
小说结尾写下“大雪里温暖如春”
封面新闻:有评论将《塞影记》与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陈忠实的《白鹿原》相提并论,称之为一脉相承、不容忽视的史诗作品。在写作的时候,你想要传达出什么?你一直追求的是怎样的艺术境界?
马平:面对蜂拥而来的评论,我一直是冷静的。鲜花和掌声让我知道,大多数读者是真心喜欢《塞影记》的。
我在写作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过程,所以,我只能通过从眼前生长出来的文字,去把我当时写下的那个句子那个段落的意义精准地传达出来。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不容出错的方向,行路到头,风景看够,我也才能知道究竟要传达什么。《塞影记》结尾我写下了“大雪里温暖如春”这个句子,才知道,我把最想说的话说了出来。这句话可以总结主人公雷高汉的一生,也大致可以说明我所追求的艺术境界,那就是哪怕用一场雪来布置,也同样要让人感受到春天一般的温暖。
封面新闻:《塞影记》细节纷繁,人物众多,你是怎么把他们捋顺的?这种把控情节、讲故事的能力不是谁都有。你觉得自己是天赋多一些还是后天训练多一些?
马平:《塞影记》针头线脑难捋难顺,但这也正好给了作家一个挑战的机会。我没有制订创作提纲的习惯,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同时走一步看千里。我眼前屏幕上冒出来的那一行行文字,是我用脑海里那不时翻卷的风暴,把它们从一个神秘的地方召唤回来的。我并不知道我是不是拥有你所说的这个能力,即使有,我也并不知道这属于先天还是后天。我只知道,一路走下来,我那个看一步或是看千里的姿态,好像比从前轻松了许多。
打开这本书“希望读者读到开阔”
封面新闻:《塞影记》和《高腔》都写到了川剧。川剧这种艺术形式,对你的艺术滋养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平:川剧给我的艺术滋养,首要的还是乡音俚语,它们敲锣打鼓助威,好像让我有了把四川风味表现出来的底气。其次,某一折川剧总能和我讲述的某一个故事会面,至少有《高腔》和《塞影记》这两回,它们好像并没有通过我脑海那必经之路,而是直接现身说法。事实上,进入中年以后,我就很少有机会去戏院看川剧了,但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大概比别人多了一份幸运,拥有一大摞可遇而不可求的剧本。白纸黑字,这让我的底气更加充足了。
封面新闻:作为作者,你最希望读者从《塞影记》获得怎样的东西?
马平:我最希望读者从《塞影记》中获得的,是开阔。鸿祯塞虽大,但毕竟在这个浩瀚无垠的世界上,它又是那样微不足道。我要做的工作,或者说我对读者的阅读期待,就是把它打开。打开一本书,打开一座塞,打开一方水土,进而打开一个世界。
乡村需要文学去表达、去建设
封面新闻:你的作品大多是乡村题材,而你现在是在城市生活。这也验证了一个道理:真正认识一个地方,往往是离开它、有了一定距离的时候。当你回望生活过的乡村,那是怎样的感情?
马平:我更愿意你把“距离”换成“阅历”或是“目力”。身居城市,说到底,还是一份与城市相关的阅历,让我的目力有了一定的增强,勉强还能够看见乡村罢了。要认识乡村就得到乡间去,就像要认识雷高汉就得到“鸿祯田庐”去,在他面前坐下来,听他唠叨不休地诉说。
封面新闻:谢有顺曾经这样评论你:“马平对乡村中国有了一个基本判断:这是一个混杂着欢乐和苦难、善良和污秽、生命与死亡、美好与丑陋、淳朴与狭隘的世界。”你对乡村生活的描绘,还是多倾向于美好的一面。这些年,由于城镇化的推进,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文化凋零,创新力不足。对于这些,你是怎么思考的?
马平:我是从乡间走出来的作家,对乡村有着一份独特的感情,或者说有着一份格外的体恤。我并不是说我总是在看乡村成绩的时候多睁一只眼睛,在看乡村问题的时候就闭上一只眼睛甚至把两只眼睛全都闭上。事实上,我的短篇小说《老松树车站》《公路上出了什么事》、中篇小说《我在夜里说话》《高腔》《我看日出的地方》和长篇小说《山谷芬芳》等作品中,就有对你所提的问题的思考。我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乡村都需要文学去表达,也需要文学去建设。
我的文学养成里,有星星彩虹神女峰
封面新闻:作家张炜曾经说:“在碎片化的网络数字时代,哪怕写下来一个自然段,甚至是一句话,你要有很多的理由才能把读者挽留住,才能让他在你的文字面前驻足,你的读者才不会流失,要做到这个很难。”你觉得这给作家带来怎样的挑战?
马平: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这是白居易的两句诗。我想,要把读者挽留住,你就得做一堆火,而不做那眨眼之间只给你留下一团漆黑的萤火虫;你得做一颗珍珠,而不做那眨眼之间只给你留下一片呆叶的露珠。我还想说的是,一个作家,应该有文字的洁癖。这本就是一个挑战,连这个挑战都对付不了,还敢奢求战胜别的什么呢?
封面新闻:你对文学的敏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发的?你的文学养成有着怎样的故事?
马平: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星星,在院坝里搭一张簸箕,仰面朝天睡在里面,需要大人反复督促才会进屋睡觉。还有一次,我疯跑着去追彩虹。但是,那些时候,我离文学还远得很。三十年前,我已经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被一家刊物组织到三峡采风,我们乘坐的船停靠在神女峰对岸,其他人都去村里参观了,我不愿去重复那些我一心想走出来的乡下生活,就在岸边一块石头上躺下来,一动不动向上望着神女峰,那些人在村里待了多久,我就那样望了多久,直到泪水夺眶而出。我是说,我的文学养成的故事里面,有星星,有彩虹,还有神女峰。而我对文学的敏感的触发,大概就在泪水夺眶而出的那一刻。还有,在我开始写作以后,再仰面朝天睡在簸箕里,发现脚已经伸到了簸箕外面,它的边缘硌痛了我的小腿那一刻。
封面新闻:一个作家该如何保持新鲜感,而不是变成惯性写作?请你分享一些经验。就你本人来说,对写作方面还存在怎样的愿景,以及目前存在的一些困惑、难题?
马平:我每一部新作的创作,都如同一次相亲,但我知道不能犯重婚。不断地重复自己,却还要贴上福克纳那样的“邮票”,贴上突破和创新这样的标签,谁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我没有什么经验可谈。我的愿景是,高山里能够拉出一片平原,平原上能够矗立起一座高山。这也是我面临的难题,因为我并不知道,平原和高山,我到底更加倾情于哪一个。
诗不在远方,它就在三尺以内萦绕
封面新闻:文学是一种特别注重个性和语言创新的艺术形式。据你这么多年进行语言实验的心得体会,对于那些刚刚写作不久的年轻人,避免陈词滥调,有哪些建议?
马平:我偶尔写旧体诗,不写现代诗,要我来提建议是危险的,我可不能冒这个险。但是,关于诗意,我还是有话可说。我们常说“诗和远方”,恍一听好像诗已经去了远方,其实,诗就在我们身边,诗意就在三尺以内萦绕。避免陈词滥调,并不是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样弄不好反倒会哗众取宠。我的意见是,说话也好,写文章写诗也好,首要的是恰切,不人云亦云,这就是不走弯路。一句话,诗意并不是要你作诗,话语恰切,诗意自生。
封面新闻:阅读哪些文学作品对你走向文学创作起到的意义比较大?就你的体会来说,阅读跟写作是怎样的关系?
马平:小时候,《水浒传》对我影响巨大。开始创作以后,我最早读文学杂志,上世纪80年代活跃在文学界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我差不多都喜欢。后来,我的阅读兴趣转到了国外。
我认为,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既不是功夫秘笈与练武功的关系,也不是藏宝图和探宝的关系。写作离不开阅读,但阅读显然不是仅为写作而存在。一个写作者的专业阅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功利在里面,但那是需要尽力去克服的。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写作者的阅读姿势,应该和普通读者一样,也许他能够获取的,会和他在写作中获取的一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