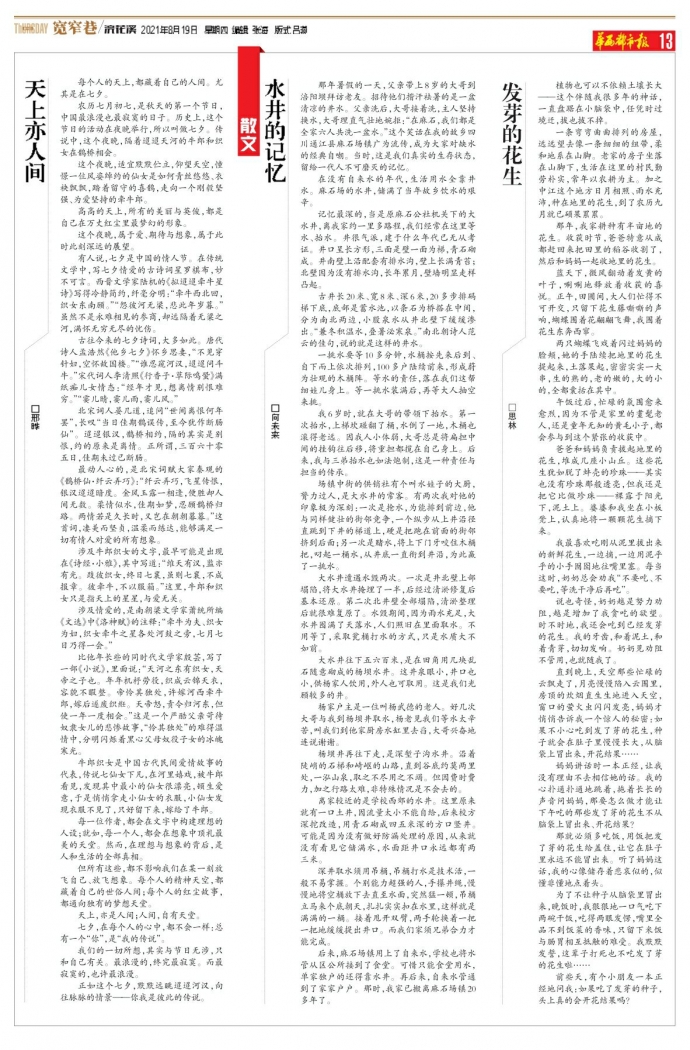水井的记忆
□ 向未来
那年暑假的一天,父亲带上8岁的大哥到涪阳坝拜访老友。招待他们揩汗祛暑的是一盆清凉的井水。父亲洗后,大哥接着洗,主人坚持换水,大哥理直气壮地婉拒:“在麻石,我们都是全家六人共洗一盆水。”这个笑话在我的故乡四川通江县麻石场镇广为流传,成为大家对缺水的经典自嘲。当时,这是我们真实的生存状态,留给一代人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生活用水全靠井水。麻石场的水井,储满了当年故乡饮水的艰辛。
记忆最深的,当是原麻石公社机关下的大水井,离我家约一里多路程,我们经常在这里等水、抬水。井很气派,建于什么年代已无从考证。井口呈长方形,三面是壁一面为梯,青石砌成。井南壁上沿配套有排水沟,壁上长满青苔;北壁因为没有排水沟,长年累月,壁墙明显走样凸起。
古井长20米、宽8米、深6米,20多步排码梯下底,底部是蓄水池,以条石为桥搭在中间,分为南北两边,小股泉水从井北壁下缓缓渗出。“兼冬积温水,叠暑泌寒泉。”南北朝诗人范云的佳句,说的就是这样的井水。
一挑水要等10多分钟,水桶按先来后到、自下而上依次排列,100多户陆续前来,形成蔚为壮观的木桶阵。等水的责任,落在我们这帮细娃儿身上。等一挑水装满后,再等大人抽空来挑。
我6岁时,就在大哥的带领下抬水。第一次抬水,上梯坎碰翻了桶,水倒了一地,木桶也滚得老远。因我人小体弱,大哥总是将扁担中间的挂钩往后移,将重担都揽在自己身上。后来,我与三弟抬水也如法炮制,这是一种责任与担当的传承。
场镇中街的供销社有个叫水娃子的大厨,膂力过人,是大水井的常客。有两次我对他的印象极为深刻:一次是抢水,为能排到前边,他与同样健壮的街邻竞争,一个纵步从上井沿径直跳到下井的梯道上,硬是把跑在前面的街邻挤到后面;另一次是赌水,将上下门牙咬住木桶把,叼起一桶水,从井底一直衔到井沿,为此赢了一挑水。
大水井遭遇水毁两次。一次是井北壁上部塌陷,将大水井掩埋了一半,后经过清淤修复后基本还原。第二次北井壁全部塌陷,清淤整理后就很难复原了。水毁期间,因为雨水充足,大水井囤满了天落水,人们照旧在里面取水。不用等了,采取瓮桶打水的方式,只是水质大不如前。
大水井往下五六百米,是在田角用几块乱石随意砌成的杨坝水井。这井泉眼小,井口也小,供杨家人饮用,外人也可取用。这是我们光顾较多的井。
杨家户主是一位叫杨武德的老人。好几次大哥与我到杨坝井取水,杨老见我们等水太辛苦,叫我们到他家厨房水缸里去舀,大哥兴奋地连说谢谢。
杨坝井再往下走,是深堑子沟水井。沿着陡峭的石梯和崎岖的山路,直到谷底约莫两里处,一泓山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因费时费力,加之行路太难,非特殊情况是不会去的。
离家较近的是学校西郊的水井。这里原来就有一口土井,因流量太小不能自给,后来校方深挖改造,用青石砌成四五米深的方口竖井。可能是因为没有做好防漏处理的原因,从来就没有看见它储满水,水面距井口永远都有两三米。
深井取水须用吊桶,吊桶打水是技术活,一般不易掌握。个别能力超强的人,手攥井绳,慢慢地将空桶放下去直至水面,突然猛一顿,吊桶立马来个底朝天,扎扎实实扣在水里,这样就是满满的一桶。接着甩开双臂,两手轮换着一把一把地缓缓提出井口。而我们家须兄弟合力才能完成。
后来,麻石场镇用上了自来水,学校也将水管从区公所接到了食堂。可惜只能食堂用水,单家独户的还得靠水井。再后来,自来水管通到了家家户户。那时,我家已搬离麻石场镇2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