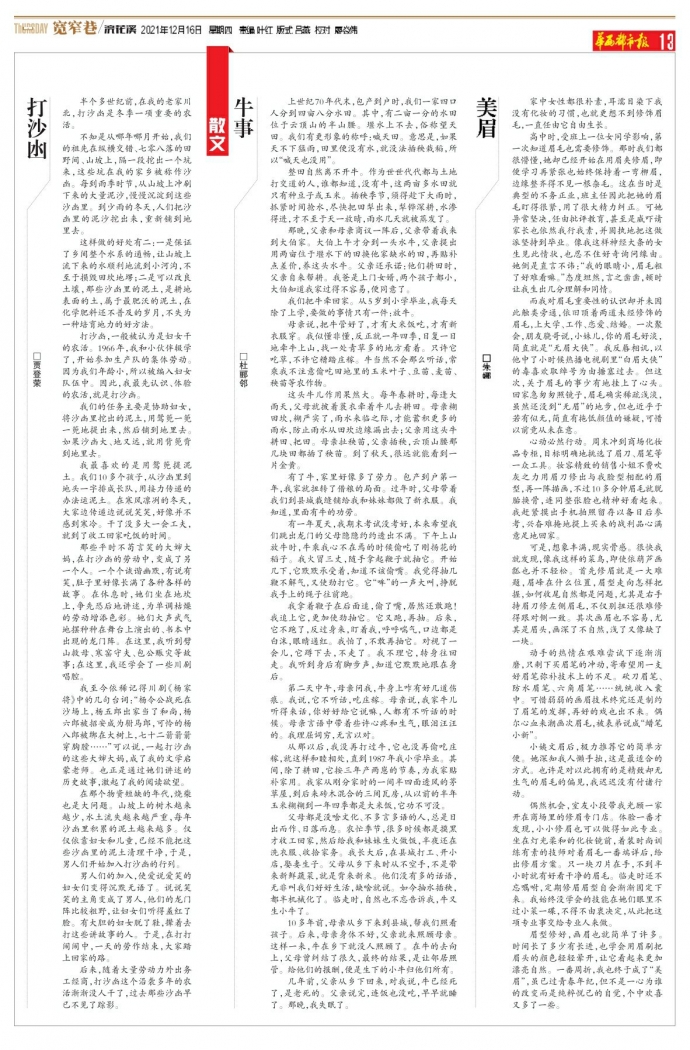打沙凼
□贾登荣
半个多世纪前,在我的老家川北,打沙凼是冬季一项重要的农活。
不知是从哪年哪月开始,我们的祖先在纵横交错、七零八落的田野间、山坡上,隔一段挖出一个坑来,这些坑在我的家乡被称作沙凼。每到雨季时节,从山坡上冲刷下来的大量泥沙,慢慢沉淀到这些沙凼里。到少雨的冬天,人们把沙凼里的泥沙挖出来,重新铺到地里去。
这样做的好处有二:一是保证了乡间整个水系的通畅,让山坡上流下来的水顺利地流到小河沟,不至于损毁田坎地塄;二是可以改良土壤,那些沙凼里的泥土,是耕地表面的土,属于最肥沃的泥土,在化学肥料还不普及的岁月,不失为一种培育地力的好方法。
打沙凼,一般被认为是妇女干的农活。1966年,我和小伙伴辍学了,开始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因为我们年龄小,所以被编入妇女队伍中。因此,我最先认识、体验的农活,就是打沙凼。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协助妇女,将沙凼里挖出的泥土,用鸳篼一篼一篼地提出来,然后铺到地里去。如果沙凼大、地又远,就用背篼背到地里去。
我最喜欢的是用鸳篼提泥土。我们10多个孩子,从沙凼里到地头一字排成长队,用接力传递的办法运泥土。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大家边传递边说说笑笑,好像并不感到寒冷。干了没多大一会工夫,就到了收工回家吃饭的时间。
那些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婶大妈,在打沙凼的劳动中,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个诙谐幽默,有说有笑,肚子里好像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在休息时,她们坐在地坎上,争先恐后地讲述,为单调枯燥的劳动增添色彩。她们大声武气地摆种种在舞台上演出的、书本中出现的龙门阵。在这里,我听到劈山救母、寒窑守夫、包公赈灾等故事;在这里,我还学会了一些川剧唱腔。
我至今依稀记得川剧《杨家将》中的几句台词:“杨令公战死在沙场上,杨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六郎被招安成为驸马郎,可怜的杨八郎被绑在大树上,七十二箭箭箭穿胸膛……”可以说,一起打沙凼的这些大婶大妈,成了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也正是通过她们讲述的历史故事,激起了我的阅读欲望。
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烧柴也是大问题。山坡上的树木越来越少,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每年沙凼里积累的泥土越来越多。仅仅依靠妇女和儿童,已经不能把这些沙凼里的泥土清理干净,于是,男人们开始加入打沙凼的行列。
男人们的加入,使爱说爱笑的妇女们变得沉默无语了。说说笑笑的主角变成了男人,他们的龙门阵比较粗野,让妇女们听得羞红了脸。有大胆的妇女脱了鞋,撵着去打这些讲故事的人。于是,在打打闹闹中,一天的劳作结束,大家踏上回家的路。
后来,随着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打沙凼这个沿袭多年的农活渐渐没人干了,过去那些沙凼早已不见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