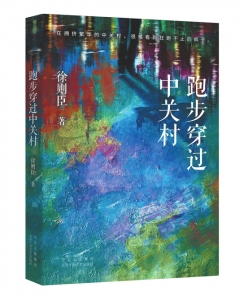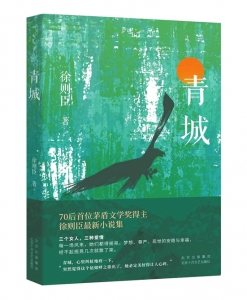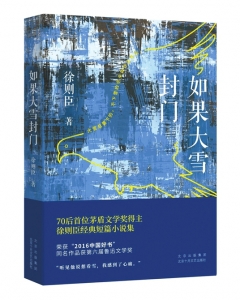小说家徐则臣:
不断地朝理想的好作品靠近
徐则臣
《跑步穿过中关村》
《青城》
《如果大雪封门》
70后作家徐则臣沉稳、勤奋,堪称文学圈劳模。虽然年纪不大,但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已经双双在手。显然,他的文学世界还正在向广阔处延伸,展现出更丰富的图景。与此同时,他还是《人民文学》副主编,是一名文学的捕手,始终在当代中国文学界保持高度在场。
西夏、居延、青城组成“三姐妹”
2021年秋,徐则臣推出最新小说集《青城》,与此同时他还修订再版经典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青城》收入《西夏》《居延》及同名短篇小说《青城》。三部作品彼此独立,又内在相连,主人公都是现代女性——西夏,居延,青城。
显而易见,三位女性的命名都与地名有关。西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近两百年的神秘王朝,居延是古代西北地区的一处军事重镇,青城则是地处四川的一座名山。这种取名寄予着作者的一种文化与历史情愫,但更多的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神来之思。
作者藉饱含历史意味的古地名作为人物的精神符号,探讨着现代女性的情感与精神自洽问题。三篇哀伤又清澈的爱情故事,讲述了三位女性的情感遭际,道尽了她们的艰难、辛酸、迷茫与坚执,也写出了她们的正直、坚韧、善良与仁爱。
“西夏,居延,青城,三个词放在一起是多么合适,三姐妹聚在一起是多么美好。”徐则臣说。
身为四川读者,让人尤其好奇《青城》这篇的写作缘由,徐则臣说:“我去过杜甫草堂,也了解过成都的地形、历史和杜甫当年来浣花溪边置茅屋过生活的传奇;穿行在公园曲折的小路上,又想起有一年我去峨眉山路上,头脑中冒出的‘青城’,心里纠扯地疼一下,突然觉得这个姑娘呼之欲出了,她必定美好得让人心碎。就她了,回来开始写《青城》。”
《青城》是深具社会性别意识的写作
男作家写小说以女子为主角,总是被格外关注。比如毕飞宇因为写《玉米》,被认为是非常懂女人的作家。
在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看来,徐则臣的新作《青城》是深具社会性别意识的写作,她认为一方面显示出这位作家经过时间的淘洗,对男女关系复杂性的理解,已经不是二元对立的思考了。徐则臣写出了今天这个时代的女性更为复杂的生存状态,一方面能感觉到她们身上的美好、奉献,同时也可以看到她们身上非常刚性、非常有骨头的一面。
“因为男性书写里关于女性通常是两种类型,一个是天使,一个是荡妇。其实在这两种类型之外,中国文学史自古以来还有一种女性的类型,就是飞蛾扑火式的女性,她奉献,她隐忍,像地母一样,但同时有她的刚烈性,比如窦娥冤、杜丽娘死而复生,死了也要战斗到底的精神。西夏、居延和青城,她们虽然受困于某种困境,但是在细微处可以看到她们对自身命运和困境的反抗。”
小说《如果大雪封门》曾荣膺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故事以几位青年打工者在北京的生活为底子,以精细绵密的语言和出人意表的想象,讲述了梦想与现实、温情与伤害、自由与限度相纠结。对几位来自南方乡村的青年来说,大都市的生活恍若梦境,现实却不免艰难,但他们一直生活得认真严肃,满怀理想。
《跑步穿过中关村》包含了关于“北京”主题的三篇中篇小说,分别是《啊,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三篇作品均讲述了漂泊在北京、处于社会基层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跑步穿过中关村》自问世以来,温暖了许多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的心。“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的地名,也逐渐成为一些年轻人对于北京的向往地标。
对话
近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徐则臣,听他讲述写作及文学。
成都是很适合进入文学的地方
1.创作要修辞立其诚,评论亦如是
封面新闻:《青城》这个小说的气质让人很喜欢,有一种清幽的文字气息。让我好奇的是,小说里纷繁的细节应该也是从生活中来的,您是怎么缝补它们成为一个作品的?
徐则臣:
“清幽”这个词用得好。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是成都,不熟悉成都的人可能一下子找不到这个感觉。当然,我写的不是春熙路和宽窄巷子。小说完全是从生活中来的,但生活又不能整块地往小说里搬,需要铁,又不能动用巨型铁板、铁块,那就手持故事的磁铁走进生活,走进成都的街巷,无数细节的铁钉、铁屑便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奔凑而来。这些细节是我见过的、听过的、想象过的,根据需要我再重新冶炼、锻打,然后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就成了现在的《青城》。我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笔记本,看到好玩的,或者有什么新想法,会随手记下来。有的用得上,有的就永远待在笔记本上了。
封面新闻:《西夏》和《居延》出过单行本吗?
徐则臣:
没有,但之前收过其他的集子。《青城》这是第一次进书里边。我还是挺高兴的。成都这个地方还真是挺滋养人的。成都很适合进入文学。
封面新闻:文艺评论界有很多关于您作品的评论,您怎么看待这些评论?它们会给您带来什么影响吗?
徐则臣:
小说写作之余,我也会写评论,评论的难度和它之于写作的意义我很清楚,所以我充分尊重评论和评论家。不管是批评还是褒奖,我都希望看到评论家能秉持一种对作品和作家的理解与体贴之心,建设性地展开自己的评论和判断。批评没问题,连几句批评都扛不住,作家也不要当了。我反对的是有预设的批评,更反对诛心之论。创作要修辞立其诚,评论同样要修辞立其诚。我比较幸运,目前看到对我的评论基本上都是善意的,有建设性的,这些评论对我是很好的引导和启发,即使个别矫枉过正、用力过猛的,也是很好的提醒。我不迷信评论,但我的确相信好评论的能力和意义。
2.文学与时代应“若即若离,又即又离”
封面新闻:有人说文学是超前,或者是等世事沉淀以后的事情。总之要跟当下的现实保持一定距离,才能看得清。在您看来,文学跟作家自己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徐则臣:
我觉得更合适的关系应该是:若即若离,又即又离。不即,深入不进生活和时代的肌理,很多东西你是看不清的,最后只能隔靴搔痒。如果不离,进去了出不来,缺少一个足够冷静的距离,很可能当局者迷,受制于当下和眼前。好的状态是进得去出得来,离时能若即,即时又能若离。这个分寸的确不太好把握,所以它是一个作家毕生的功课。
封面新闻:您之前的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现在进行全新修订、精装再版,虽然我们都知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在您看来,这两本书会打动读者的点在哪儿?
徐则臣:
首先是来自生活的质感,我希望能够把生活与我们劈面相逢时那种粗粝的摩擦感写出来。轻飘飘一掠而过的生活、脚踩在上面打滑的生活,不值得过,也不值得写。我想把这种生活的感觉找出来,再把这种生活作用于人的精神和生活的典型状态找出来。生活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人物也要能让读者产生共鸣。然后就是我的“修辞立其诚”。我相信读者也愿意在文字中看到作者的真诚。真诚不仅仅是认真的写作态度,还是作者对生活、对人物、对问题的真实的坚守。
3.不好高骛远,一步一个脚印走就是了
封面新闻:您已经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像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一些在文学界非常有重量的奖项。当下您也正处于写作生涯的上升时期,我们都知道这个上坡的过程往往是不容易的,需要付出很多。在这个过程中有遇到怎样的困惑或者挑战?是怎么克服的?
徐则臣:
我写作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只是喜欢,也享受那种闷着头沉在里面写的感觉。既然是由衷的喜欢,困难和挑战说到底都不是问题,任何事都免不了有障碍,它是做事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不好高骛远,也不着急,一步一个脚印走就是了,愿意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也时刻提醒自己顺其自然,保持一颗平常心。写作本身的困难打不倒我,倒是偶尔出现的虚妄之感要花点时间去排解。其实这也是老生常谈,很多人在写作之初就解决了写作的意义的问题;很惭愧,写了二十多年了,我还经常被这个问题纠缠。
封面新闻:艺无止境,您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作家,对自己有高标准和高要求,那您接下来对写作有什么规划或者期待呢?
徐则臣:
我对文学有自己的理解,对自己的写作肯定也有一定的标准和要求。这些年我的写作一直在变、在调整,就是按照我对文学的理解,不断地朝我理想的好作品靠近。这个路会很漫长,但我能看见自己一步一个的脚印,为此挺欣慰。我正在写的,和我同时在准备的,有好几部作品,有长篇小说,也有短篇小说集,每一本书都试图解决我的一部分问题,实现我对好作品的一部分想法。我从不期待一部作品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不现实,我也不喜欢,我更喜欢一部一部逼近、从四面合围的感觉。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实习生李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