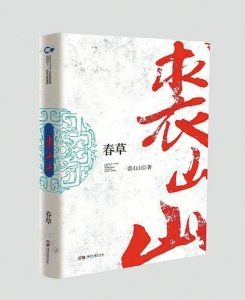裘山山式“纯棉写作”:用朴素的语言书写普通人的生活
裘山山(本人供图)
《春草》
1976年,裘山山入伍,当了一名通讯兵。她喜欢阅读,对精神食粮感到饥渴。可连队阅览室大部分都是技术类图书,她喜欢看的文学书少得可怜。她给报纸写稿得了7元钱稿费,就去新华书店买了想看的书,捐给连队阅览室,然后再借出来看。后来她发现连队旁边有一个区图书馆,于是星期天请假,拿着连队文书开的证明去借书看。那时候读书,毫无功利心,也不需要人督促,就是喜欢,就是入迷。当然读多了,就想写了。
心里埋下当作家的种子
裘山山是有文学写作的因缘的。她父亲是铁路工程师,对文学也有赤诚的热爱和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母亲是浙江日报的老编辑,很有写作才华。知识分子家庭对她有无形的熏陶。读中学时,裘山山作文就写得好,老师经常在班上念她的作文,她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将来当个作家”的种子。
当了兵,部队很重视写作才能。裘山山因此经常被抽调参加报道培训班。有一次她写了一篇散文《我们女战士》,投给重庆日报,被采用了。收到样报和两本充当稿费的稿纸那天,正好是她生日。这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稿子变成“铅字”,这让她觉得“似乎是一种预言”,自己可以走写作这条路。大学毕业后的1984年,她终于在《昆仑》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那是她的处女作。
从18岁到58岁,一生最美好的年华,裘山山都是在部队度过的。身为军旅作家,她曾多次进藏,翻山越岭去往雪域边关,最终写成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铁血柔情荡气回肠,影响深远。“因为看了《我在天堂等你》,军校毕业时申请去高原,这样的故事我听到过几次了。”这部作品多次再版,还被改编成不同的艺术体裁。
但裘山山说,其实她不太会写重大题材、冲突强烈的小说,当时之所以会写《我在天堂等你》,是因为自己多次上高原,获得了真实的感动,促使她不得不拿起笔来写这批可敬可爱的人。其实她更多的作品,是写市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比如长篇小说《到处都是寂寞心》,短篇小说《曹德万出门去找爱情》《课间休息》《大雨倾盆》《腊八粥》《我需要和你谈谈》等,都是名篇。
“裘式风格”是怎么形成的
读大学时,裘山山读到两位俄国作家的作品,一个是艾特玛托夫,一个是帕乌斯托夫斯基。他们俩讲故事的风格都是平和、缓慢、深沉的,在不疾不徐的节奏中营造出一种氛围,带读者进入故事里去。他们的影响力远不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但是裘山山觉得很对胃口,甚至有点迷恋那种“有一点忧伤又有一种宁静”的调子,她就学着那个味道开始写短篇。
为了学习如何结尾,她又去图书馆里找了一本《王汶石短篇小说选》,读来也很喜欢,平实的语言,老老实实的故事,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却充满了生活气息。她喜欢的作家哈金,讲平常的事,写普通人生活里蕴含的丰富况味。她还欣赏一些日本作家的写法,散淡平和。
“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包裹丰富的内涵。”这样的审美观念逐渐在裘山山心里形成。她自己的文学创作自然也往这个方面靠。久而久之,“裘氏风格”就形成了:行文清爽质朴、从容不迫;恰到好处的机智幽默;峰回路转、却又不露痕迹的架构。小说中的人物、事件或者故事,都是非常普通、日常的。然而就是在普通人身上,裘山山写出了令人咂摸不尽的平中见奇,所以她的这些写作也被称为“纯棉写作”。
一流的文学往往依靠的不是题材的宏大,而在于怎么写,写出了什么。此外,说到底,人生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大部分是日常的细节,就算是大时代,人活的还是一个一个日常瞬间。
内心具有很强的向善性向光性
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在选材上的偏好,与其生活阅历、情感方式、文化修养乃至价值取向有很大关系。裘山山对日常生活的执着关注,也跟她的生活经历有关,“我一直生活在相对平静的生活秩序中,在父亲去世前,没有遭遇过重大的人生坎坷,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苦难,这种平顺可能就造成了我心态的平和,也影响了我对那些非常重大的或者尖锐的事件发生兴趣。”
评论家李美皆对裘山山有一番这样的评价:“裘山山的教养和经历使她的内心具有很强的向善性、向光性、母性,呈现为某种质感,就是秋日沉淀的沙床,正午温厚的河水。这种温厚的内在沉淀,使她能够在创作中对人性加以温暖的守护。”
裘山山自认自己的个性气质“在艺术家和主妇之间,更接近于主妇,比较生活化,所以我喜欢写很贴近现实的故事。对于那种很深邃、很抽象、很哲理的东西,天生有点儿畏惧,只好敬而远之。很玄幻的题材,穿越什么的,也不会写。同时对那种恶的东西,也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但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有意思的、有意义的东西并写成小说,可不是件容易事。甚至可以说,比写大开大合的戏剧化人物、事件更难。这需要非同寻常的发现力和敏感力,以及对生活有足够的热情。
裘山山说:“不要小看短篇,一个小切口,一样会有痛感。不以善小而不为,用在写作上也是可以的。生活中最普通的情感:喜悦、哀伤、嫉妒、内疚、思念、郁闷、忐忑不安,都是人性的折射。所以我认为,要写好短篇,第一就是不能轻视它,而是要热爱它、喜欢它。只有你喜欢,才能沉住气,去发现生活中那些微小的却有价值的事情。”
语言是小说极其重要的要素。一篇小说是怎样的文风,一看便知,喜欢还是不喜欢读,读不读得下去,就像人的长相、气质一样。
裘山山的小说语言不是那种拽词的、刻意凹造型的路子,她真是文如其人,实诚,朴素,干净,蕴含着思考的力量。比如在《大雨倾盆》中,她这样结尾:“路灯依然明明灭灭,有些诡异。他独自往家走,路边七零八落地掉了些断裂的树枝,还有被雨刮倒的自行车、广告牌,显得有些狼狈。他忽然想起刚才田青青说的话,有时候,老天下一场大雨,就是看到这个世界太脏了,需要洗一洗,冲一冲。可是老天却不知道,这世界是那么不经洗,一冲刷,真相到处显露。”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