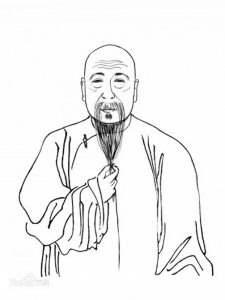清代天坛望灯杆采办大费周章 川西26根“贡木”竟耗银30万两
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吴棠像
天坛望灯杆原本是三个。1914年12月,袁世凯祭天时因望灯杆糟朽而拆掉了其中的两根灯杆。此照片是1935年林徽因与古建专家们爬上祈年殿顶所拍摄。
《申报》所载吴棠的奏章。作者供图
□周德富
四川盛产优质木材。自古以来,川木就是宫廷建筑的首选,这从杜牧的《阿房宫赋》“蜀山兀,阿房出”即可窥见一斑。而历经同治、光绪两朝,长达十多年的采办天坛望灯杆木之事则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祷丰年的地方,在皇帝眼中这是一个极其神圣的场地,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故宫、地坛等场馆,自然都很重视其建设和维护。天坛望灯是天坛的一个标志性设施。
泸定寻获可做望灯杆之材
官员贾鑫督运贡木遇险而亡
清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工部给皇帝上奏,反映天坛的望灯杆木出现了裂纹和空洞,需要修补和更换,但维修的木厂却无可用之木,希望朝廷给四川和湖广下诏,让他们派员“购备头梢匀直,长十丈以外,大径二尺七寸,小径一尺二寸正副杆木六根,长六丈以外戗木十八根运解至京”。所谓的“头梢匀直”就是说从根到梢,整根木头要非常端直且均匀,“大径”是指下端的直径,“梢径”是指上端的直径,“戗木”又称“戗柱”,是指支撑杆木的斜柱。天坛的望灯是三座,每座是一杆三戗。所谓的“副”即备用。三座望灯共十二根,加上备用的一套,故需二十四根。
奏章获得了同治皇帝的批准。时任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吴棠对此非常重视,先后多次派人采办,但屡采未得,不得不多次具奏说明。其实朝廷也知道此事的难度,乾隆年间就因大木难求,曾将灯杆的长度减短。直到同治十年(1871年),事情才出现转机。吴棠将这个棘手的任务交给了时任江安县(今属宜宾市)知县贾鑫。贾鑫先后多次到川西寻找高大笔直之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贾鑫终于在沈边土司界内(今属泸定)的烟雾沟、青苔坎等地全数采获这些木材。这些长达三十多米的巨大木材在古代是不可能陆运的,只能水运,但得木的地方离大渡河甚远,运送极其困难。贾鑫只得督率民夫“凿山开道,竭力挽运”。贾鑫不辞劳苦,想尽各种办法,终于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将这批贡木运抵大渡河边。但水运也并非易事,大渡河沿河处处皆是险滩,乱石嶙峋,水势湍急,舟楫难施,只能逐根顺水漂放。考虑到这些珍贵贡木来之不易,贾鑫放心不下,于是他冒险乘坐竹筏亲自督运,不料发生意外。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十三日(一说二十三日),他的坐筏行至当时雅安县属的白水淤(一作“白水漩”)这个地方,因滩高浪急,被冲撞折断,他本人当即溺水遇难,随行的四名轿夫、一名跟役也溺水而亡。所运木材因为失去了人的控制,在狂澜乱石之中不断磕撞,损毁极其严重,仅有十一根戗木还勉强可用,其余六根正副杆木、七根戗木都被水石冲激,损毁折断,已不符合维修天坛望灯杆木的尺寸要求,必须重新采办。
吴棠迅速将此事上奏朝廷,同时火速把巫山县知县武震招来接办此事。武震驰任之后,立即前往烟雾沟、青苔坎等处查看,结果发现这些地方已无可采之木。武震只得扩大寻找范围。光绪元年(1875年)秋天,武震终于在今属雅安市石棉县的王冈坪(即今王岗坪)的深山老林里发现了一批坚直大木。吴棠当即决定,一方面马上开工砍伐,一方面迅速向朝廷报告,要求朝廷宽限送达的时间。光绪二年(1876年)开春之后,武震迅速组织人员进入王冈坪伐木,并想尽一切办法向外运送。八月,武震终于将合朝廷所需贡木运抵嘉定府治(今乐山)所在的入江之口,交付嘉定府知府玉崐点验。经玉崐点验,这批贡木的丈尺、根数等与工部要求完全相符。
运送“王木”的木筏蔽江而来
在长江上走了一年零三个月
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十三日,编扎好的巨型木筏从嘉定府治江边起程。这次运送仍由武震负责,考虑到程远责重,增加了嘉定府试用通判庄思恒帮同运解。木筏沿岷江顺流而下,然后顺着长江主河道,前往目的地江苏省上海县。起运之前吴棠已经去世,接任四川总督的是满清皇室宗亲文格,他要求四川省沿江各州县逐程派人护送木材,所需各项费用在全省文职知县以上官员的养廉银中统一摊扣。他还上奏朝廷,希望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勅下两江督臣和江苏巡抚,让他们指示上海道台及当时中国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总局”察看情形,并委派当地要员协调办理。
清末学者陈锦在其光绪四年(1878年)刊刻的《勤余文牍》中记载:“梗楠杞梓,自楚出也,庇材者麇集于汉。乾嘉以前,闲岁易天坛灯杆,构大材,不于藏则于川。巨筏蔽江,名曰‘王木’。”这段文字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运送“王木”的木筏蔽江而来的壮观场景。明万历年间刘戡之的《大木行序》却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壮观背后的艰辛和酸楚:“万历丙申来,宫殿灾先后相继,离宫别殿,无岁不灾,以故用材之广也。西蜀大木蔽江而下,流连道路……余辛丑秋舟次下邳(今属江苏),偶遇乘桴(此指木筏),鹄立健儿则肤无皮,指无爪,腓无毛,相向欷歔。”这些在长江上长途押运“大木”的船工竟然都“肤无皮,指无爪,腓无毛”,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这批贡木出川之后是否顺利到达上海?何时到达上海?贡木有无丢失?这些信息在光绪四年(1878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海《申报》登载的《招运天坛灯杆木》启事中得到了较为详细的披露:启者兹有天坛灯杆木共正副二十六根,业已抵沪,拟由海道运至天津紫竹林交缷,无论轮船、夹舨,有愿领运者,可将运费船价开明,务于本月二十九日以前送至本局,以凭核办。
从这则启事我们不难看出,武震他们押着巨型木筏在长江上走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最终把这批贡木安全送到了上海,并且他们还多运去了两根,实际是二十六根。
其实,上海到天津的水运,并非一定得航海,也可走大运河。之所以没有选择河运是有原因的。同治十二年(1873年),当得知贾鑫已在川西找到大木,朝廷就大木到达上海后的运送渠道作过讨论。同治皇帝还曾下过一道谕旨给河东河道总督乔松年:“川省采办天坛望灯杆木植,查照向章,应由江南瓜洲口循运河北上,中间有无阻滞?着沿途各省督抚暨运河道各总督,查明经过地方,如能照旧运河,即行饬所属,一体照料催攒,以期妥速;如运河难以行走,能否由海运解?”乔松年经过调查发现:“现在东省运道,南自郗山口进河,至运属利建口入河,复由枣林绕越西坡,纾折潆回,转湾非易。其捕属穿运处所,黄水纷歧,汶港或南或北,不能遵循。若由运河行走,不免贻误。”估计正是因为有乔松年几年前的这个调查,雅安贡木到达上海才最终选择了自沪航海运津的方案。
徐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轮船运输企业“轮船招商总局”的创建者之一,也是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的创建者,他参与了雅安贡木的投保和海运的相关工作,是最了解情况的当事人之一,事后他写了一篇《记承运天坛望灯木杆》:光绪四年(1878年)四川委员巫山县知县武震、川东试用通判庄思恒,奉两江总督沈、四川总督文札,委招商局总办承运天坛望灯木杆二十六根……可谓大而长矣。时商局旧日“伊敦”轮船经已改作趸船,即用此趸船装载,再派“永清”、“海定”两船拖带。(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
贡木运抵京城耗银30万两
当时正值山西和河南大旱灾
这次望杆木海运,由天津轮船招商局第一艘蒸汽动力商船“伊敦”号承运,这是大清航海史上最先进的运输工具,运输的却是皇家用的几根木头,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颇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荒唐。而当时的外国人对此事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光绪四年(1878年)的上海《申报》有一篇《西报论贡木》:西字日报论及天坛灯杆木事,言木共二十六根,合诸沪上价值有银二十万两左右;今从轮船拖往天津,又须三万;由津到京,又须七万。以三十万两之银,仅运二十六根之木,毋乃太形耗费乎?而况值晋豫饥民嗷嗷待哺之时乎?
可以肯定,这里说的三十万两白银应该不包括贾鑫第一次采伐、运输所用的费用,更不会包括淹死的贾鑫等六个人的抚恤金和其他社会成本等,甚至可能还不包括付给保险公司的保费。这就意味着雅安这批贡木最终运抵京城所耗费的白银一定是远远超过三十万两。当时正值山西和河南发生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而雅安这批贡木的运送就发生在这一艰难时期。朝廷不去集中财力救灾,居然耗费这么多的白银运送二十六根木料,何其荒唐!
据头品顶戴署湖广督臣裕禄、头品顶戴湖北巡抚臣彭祖贤《跪奏为拣员调补道员要缺以资治理恭摺》,武震他们最终把这批木头“运抵通州木厂交收完竣”的时间是光绪四年(1878年)十月。这就说明,由紫竹林到天津又用了接近半年时间。武震也因此而于光绪“五年三月由工部带领引见”,即被皇帝召见,后一路升迁,光绪十一年(1885年)官至汉黄德道盐法武昌道道台,这是后话。
此事虽然已经过去近150年了,但雅安的官民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可证雅安物产之丰富,故行文以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