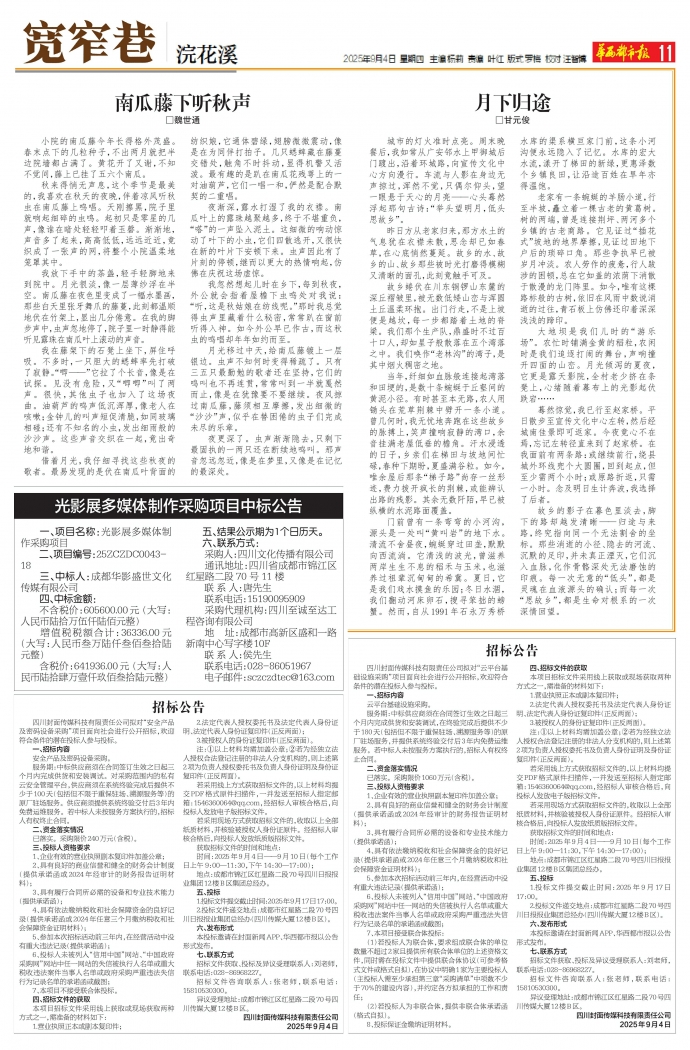月下归途
□甘元俊
城市的灯火准时点亮。周末晚餐后,我如常从广安邻水上甲御城后门踱出,沿着环城路,向宣传文化中心方向漫行。车流与人影在身边无声掠过,浑然不觉,只偶尔仰头,望一眼悬于天心的月亮——心头蓦然浮起那句古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昨日方从老家归来,那方水土的气息犹在衣襟未散,思念却已如春草,在心底悄然蔓延。故乡的水、故乡的山、故乡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模糊又清晰的面孔,此刻竟触手可及。
故乡蜷伏在川东铜锣山东麓的深丘褶皱里,被无数低矮山峦与浑圆土丘温柔环抱。出门行走,不是上坡便是越坎,每一步都踏着土地的脊梁。我们那个生产队,鼎盛时不过百十口人,却如星子般散落在五个湾落之中。我们唤作“老林沟”的湾子,是其中烟火稠密之地。
当年,纤细如血脉般连接起湾落和田埂的,是数十条蜿蜒于丘壑间的黄泥小径。有时甚至本无路,农人用锄头在荒草荆棘中劈开一条小道。曾几何时,我无忧地奔跑在这些故乡的脉搏上,笑声撞响寂静的湾口,余音挂满老屋低垂的檐角。汗水浸透的日子,乡亲们在梯田与坡地间忙碌,春种下期盼,夏盛满谷粒。如今,唯余屋后那条“梯子路”尚存一丝形迹,费力拨开疯长的荆棘,或能辨认出路的残影。其余无数阡陌,早已被纵横的水泥路面覆盖。
门前曾有一条弯弯的小河沟,源头是一处叫“黄叫岩”的地下水。清流不舍昼夜,蜿蜒穿过田垄,默默向西流淌。它清浅的波光,曾滋养两岸生生不息的稻禾与玉米,也滋养过祖辈沉甸甸的希冀。夏日,它是我们戏水摸鱼的乐园;冬日水涸,我们翻动河床卵石,搜寻笨拙的螃蟹。然而,自从1991年石永万秀桥水库的渠系横亘家门前,这条小河沟便永远隐入了记忆。水库的宏大水流,漾开了梯田的新绿,更惠泽数个乡镇良田,让沿途百姓在旱年亦得温饱。
老家有一条蜿蜒的羊肠小道,行至半坡,矗立着一棵古老的黄葛树。树的两端,曾是连接荆坪、两河多个乡镇的古老商路。它见证过“插花式”坡地的地界摩擦,见证过田地下户后的琐碎口角。那些争执早已被岁月冲淡。农人劳作的疲惫,行人跋涉的困顿,总在它如盖的浓荫下消散于散漫的龙门阵里。如今,唯有这棵路标般的古树,依旧在风雨中数说消逝的过往,青石板上仿佛还印着深深浅浅的蹄印。
大地坝是我们儿时的“游乐场”。农忙时铺满金黄的稻粒,农闲时是我们追逐打闹的舞台,声响撞开四面的山峦。月光倾泻的夏夜,它更是露天影院,全村老少挤在条凳上,心绪随着幕布上的光影起伏跌宕……
蓦然惊觉,我已行至赵家桥。平日散步至宣传文化中心左转,然后经城南佳景即可返家。今夜竟心不在焉,忘记左转径直来到了赵家桥。在我面前有两条路:或继续前行,绕县城外环线兜个大圆圈,回到起点,但至少需两个小时;或原路折返,只需 一小时。念及明日生计奔波,我选择了后者。
故乡的影子在暮色里淡去,脚下的路却越发清晰——归途与来路,终究指向同一个无法割舍的坐标。那些消逝的小径、隐去的河流、沉默的足印,并未真正湮灭,它们沉入血脉,化作骨骼深处无法磨蚀的印痕。每一次无意的“低头”,都是灵魂在血液源头的确认;而每一次“思故乡”,都是生命对根系的一次深情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