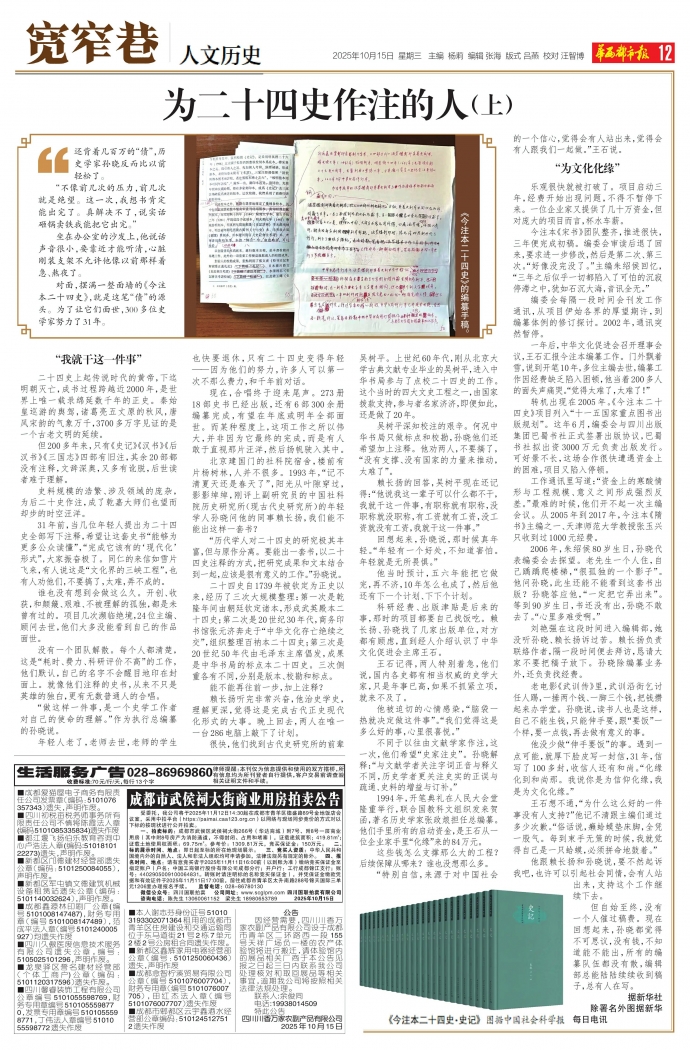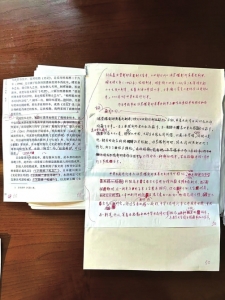为二十四史作注的人(上)
《今注本二十四史》的编纂手稿。
《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图据中国社会科学报
还背着几百万的“债”,历史学家孙晓反而比以前轻松了。
“不像前几次的压力,前几次就是绝望。这一次,我想书肯定能出完了。真解决不了,说实话砸锅卖铁我能把它出完。”
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他说话声音很小,要靠近才能听清,心脏刚装支架不允许他像以前那样着急、熬夜了。
对面,摆满一整面墙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就是这笔“债”的源头。为了让它们面世,300多位史学家努力了31年。
“我就干这一件事”
二十四史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明朝灭亡,成书过程跨越近2000年,是世界上唯一载录绵延数千年的正史。秦始皇巡游的舆驾,诸葛亮五丈原的秋风,唐风宋韵的气象万千,3700多万字见证的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延续。
但200多年来,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有旧注,其余20部都没有注释,文辞深奥,又多有讹脱,后世读者难于理解。
史料规模的浩繁、涉及领域的庞杂,为后二十史作注,成了乾嘉大师们也望而却步的时空汪洋。
31年前,当几位年轻人提出为二十四史全部写下注释,希望让这套史书“能够为更多公众读懂”,“完成它该有的‘现代化’形式”,大家振奋极了。同仁的来信如雪片飞来,有人说这是“文化界的三峡工程”,也有人劝他们,不要搞了,太难,弄不成的。
谁也没有想到会做这么久。开创、收获,和颠簸、艰难、不被理解的孤独,都是未曾有过的。项目几次濒临绝境,24位主编、顾问去世,他们大多没能看到自己的作品面世。
没有一个团队解散。每个人都清楚,这是“耗时、费力、科研评价不高”的工作,他们默认,自己的名字不会醒目地印在封面上。就像他们注释的史书,从来不只是英雄的独白,更有无数普通人的合唱。
“做这样一件事,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自己的使命的理解。”作为执行总编纂的孙晓说。
年轻人老了,老师去世,老师的学生也快要退休,只有二十四史变得年轻——因为他们的努力,许多人可以第一次不那么费力,和千年前对话。
现在,合唱终于迎来尾声。273册18部史书已经出版,还有6部300余册编纂完成,有望在年底或明年全部面世。而某种程度上,这项工作之所以伟大,并非因为它最终的完成,而是有人敢于直视那片汪洋,然后扬帆驶入其中。
北京建国门的社科院宿舍,楼前有片杨树林,人并不很多。1993年,“记不清夏天还是春天了”,阳光从叶隙穿过,影影绰绰,刚评上副研究员的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现古代史研究所)的年轻学人孙晓问他的同事赖长扬,我们能不能出这样一套书?
“历代学人对二十四史的研究极其丰富,但与原作分离。要能出一套书,以二十四史注释的方式,把研究成果和文本结合到一起,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孙晓说。
二十四史自1739年被钦定为正史以来,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整理:第一次是乾隆年间由朝廷钦定诸本,形成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第二次是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奔走于“中华文化存亡绝续之交”,组织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三次是20世纪50年代由毛泽东主席倡发,成果是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二十四史。三次侧重各有不同,分别是版本、校勘和标点。
能不能再往前一步,加上注释?赖长扬听完非常兴奋,他治史学史,理解更深,觉得这是完成古代正史现代化形式的大事。晚上回去,两人在唯一 一台286电脑上敲下了计划。
很快,他们找到古代史研究所的前辈吴树平。上世纪60年代,刚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吴树平,进入中华书局参与了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这个当时的四大文史工程之一,由国家拨款支持,参与者名家济济,即便如此,还是做了20年。
吴树平深知校注的艰辛。何况中华书局只做标点和校勘,孙晓他们还希望加上注释。他劝两人,不要搞了,“没有支撑、没有国家的力量来推动,太难了”。
赖长扬的回答,吴树平现在还记得:“他说我这一辈子可以什么都不干,我就干这一件事,有职称就有职称,没职称就没职称,有工资就有工资,没工资就没有工资,我就干这一件事。”
回想起来,孙晓说,那时候真年轻。“年轻有一个好处,不知道害怕。年轻就是无所畏惧。”
他当时预计,五六年能把它做完,再不济,10年怎么也成了,然后他还有下一个计划、下下个计划。
科研经费、出版津贴是后来的事,那时的项目都要自己找饭吃。赖长扬、孙晓找了几家出版单位,对方都有顾虑,直到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
王石记得,两人特别着急,他们说,国内各史都有相当权威的史学大家,只是年事已高,如果不抓紧立项,就来不及了。
他被迫切的心情感染,“脑袋一热就决定做这件事”。“我们觉得这是多么好的事,心里很喜悦。”
不同于以往由文献学家作注,这一次,他们希望“史家注史”。孙晓解释:“与文献学者关注字词正音与释义不同,历史学者更关注史实的正误与疏通、史料的增益与订补。”
1994年,开笔典礼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来贺函,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担任总编纂。他们手里所有的启动资金,是王石从一位企业家手里“化缘”来的84万元。
这些钱怎么支撑那么大的工程?后续保障从哪来?谁也没想那么多。
“特别自信,来源于对中国社会的一个信心,觉得会有人站出来,觉得会有人跟我们一起做。”王石说。
“为文化化缘”
乐观很快就被打破了。项目启动三年,经费开始出现问题,不得不暂停下来。一位企业家又提供了几十万资金,但对庞大的项目而言,杯水车薪。
今注本《宋书》团队整齐,推进很快,三年便完成初稿。编委会审读后退了回来,要求进一步修改,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好像没完没了。”主编朱绍侯回忆,“三年之后似乎一切都陷入了可怕的沉寂停滞之中,犹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编委会每隔一段时间会刊发工作通讯,从项目伊始各界的厚望期许,到编纂体例的修订探讨。2002年,通讯突然暂停。
一年后,中华文化促进会召开理事会议,王石汇报今注本编纂工作。门外飘着雪,说到开笔10年,多位主编去世,编纂工作因经费缺乏陷入困顿,他当着200多人的面失声痛哭。“觉得太难了,太难了!”
转机出现在2005年。《今注本二十四史》项目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这年6月,编委会与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正式签署出版协议,巴蜀书社拟出资3000万元负责出版发行。可好景不长,这场合作很快遭遇资金上的困难,项目又陷入停顿。
工作通讯里写道:“资金上的寒酸情形与工程规模、意义之间形成强烈反差。”最难的时候,他们开不起一次主编会议。从2005年到2017年,今注本《隋书》主编之一、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张玉兴只收到过1000元经费。
2006年,朱绍侯80岁生日,孙晓代表编委会去探望。老先生一个人住,自己踽踽爬楼梯,“很孤独的一个影子”。他问孙晓,此生还能不能看到这套书出版?孙晓答应他,“一定把它弄出来”。等到90岁生日,书还没有出,孙晓不敢去了。“心里多难受啊。”
刘艳强在这段时间进入编辑部,她没听孙晓、赖长扬诉过苦。赖长扬负责联络作者,隔一段时间便去拜访,恳请大家不要把稿子放下。孙晓除编纂业务外,还负责找经费。
老电影《武训传》里,武训沿街乞讨任人踢,一捶两个钱、一脚三个钱,把钱攒起来办学堂。孙晓说,读书人也是这样,自己不能生钱,只能伸手要,跟“要饭”一个样,要一点钱,再去做有意义的事。
他没少做“伸手要饭”的事。遇到一点可能,就厚下脸皮写一封信,31年,信写了100多封,收信人还有和尚。“化缘化到和尚那。我说你是为信仰化缘,我是为文化化缘。”
王石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件事没有人支持?”他记不清跟主编们道过多少次歉。“俗话说,癞蛤蟆垫床脚,全凭一股气。每到束手无策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一只蛤蟆,必须拼命地鼓着。”
他跟赖长扬和孙晓说,要不然起诉我吧,也许可以引起社会同情,会有人站出来,支持这个工作继续下去。
但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催过稿费。现在回想起来,孙晓都觉得不可思议,没有钱,不知道能不能出,所有的编纂队伍都没有散,编辑部总能陆陆续续收到稿子,总有人在写。
据新华社
除署名外图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