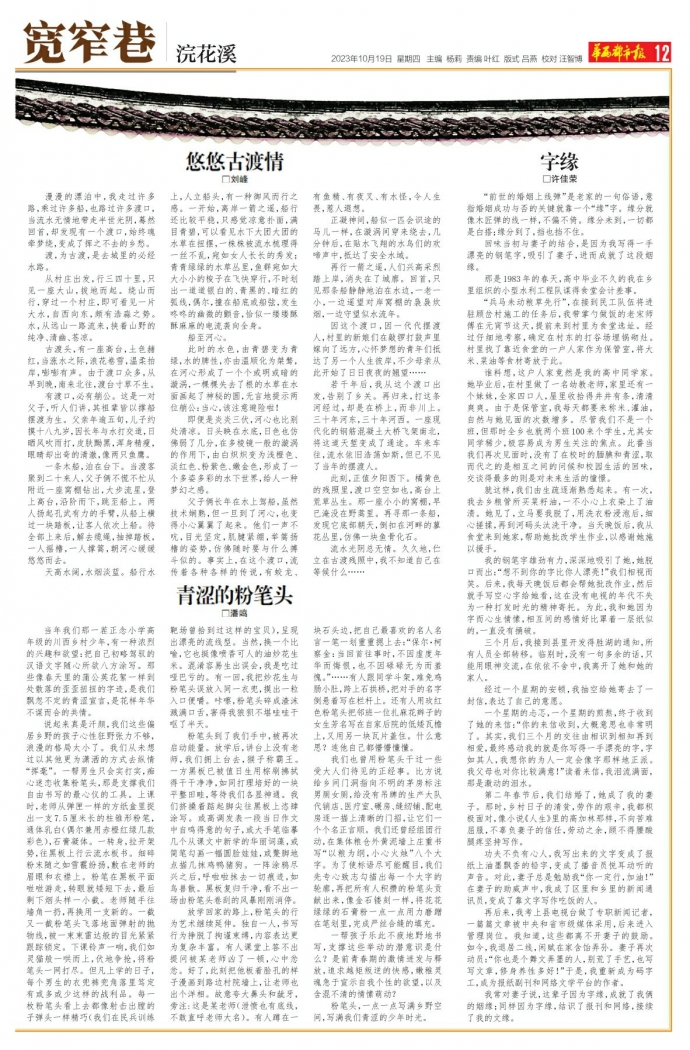悠悠古渡情
□刘峰
漫漫的漂泊中,我走过许多路,乘过许多船,也路过许多渡口,当流水无情地带走半世光阴,蓦然回首,却发现有一个渡口,始终魂牵梦绕,变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
渡,为古渡,是去城里的必经水路。
从村庄出发,行三四十里,只见一座大山,拔地而起。绕山而行,穿过一个村庄,即可看见一片大水,自西向东,颇有浩淼之势。水,从远山一路流来,挟着山野的纯净、清幽、苍凉。
古渡头,有一座高台,土色赭红,当涨水之际,浪花卷雪,温柔拍岸,嘭嘭有声。由于渡口众多,从早到晚,南来北往,渡台寸草不生。
有渡口,必有艄公。这是一对父子,听人们讲,其祖辈皆以撑船摆渡为生。父亲年逾五旬,儿子约摸十八九岁,因长年与水打交道,日晒风吹雨打,皮肤黝黑,浑身精瘦,眼睛却出奇的清澈,像两只鱼鹰。
一条木船,泊在台下。当渡客聚到二十来人,父子俩不慌不忙从附近一座窝棚钻出,大步流星,登上高台,沿阶而下,跳至船上。两人扬起孔武有力的手臂,从船上横过一块踏板,让客人依次上船。待全部上来后,解去缆绳,抽掉踏板,一人摇橹,一人撑篙,朝河心缓缓悠悠而去。
天高水阔,水烟淡蓝。船行水上,人立船头,有一种御风而行之感。一开始,离岸一箭之遥,船行还比较平稳,只感觉凉意扑面,满目青碧,可以看见水下大团大团的水草在扭摆,一株株被流水梳理得一丝不乱,宛如女人长长的秀发;青青绿绿的水草丛里,鱼群宛如大大小小的梭子在飞快穿行,不时划出一道道银白的、青黑的、暗红的弧线,偶尔,撞在船底或船弦,发生咚咚的幽微的颤音,恰似一缕缕酥酥麻麻的电流袭向全身。
船至河心。
此时的水色,由青碧变为青绿,水的脾性,亦由温顺化为桀骜,在河心形成了一个个或明或暗的漩涡,一棵棵失去了根的水草在水面画起了神秘的圆,无言地提示两位艄公:当心,该注意避险啦!
即便是炎炎三伏,河心也比别处清凉。日头映在水底,日色也仿佛弱了几分,在多棱镜一般的漩涡的作用下,由白炽炽变为浅橙色、淡红色、粉紫色、嫩金色,形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水下世界,给人一种梦幻之感。
父子俩长年在水上驾船,虽然技术娴熟,但一旦到了河心,也变得小心翼翼了起来。他们一声不吭,目光坚定,肌腱紧绷,举篙扬橹的姿势,仿佛随时要与什么搏斗似的。事实上,在这个渡口,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有蛟龙、有鱼精、有夜叉、有水怪,令人生畏,惹人遐想。
正凝神间,船似一匹会识途的马儿一样,在漩涡间穿来绕去,几分钟后,在贴水飞翔的水鸟们的欢啼声中,抵达了安全水域。
再行一箭之遥,人们兴高采烈踏上岸,消失在了城廓。回首,只见那条船静静地泊在水边,一老一小,一边遥望对岸窝棚的袅袅炊烟,一边守望似水流年。
因这个渡口,因一代代摆渡人,村里的新娘们在敲锣打鼓声里嫁向了远方,心怀梦想的青年们抵达了另一个人生彼岸,不少母亲从此开始了日日夜夜的翘望……
若干年后,我从这个渡口出发,告别了乡关。再归来,打这条河经过,却是在桥上,而非川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座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大桥飞架南北,将这道天堑变成了通途。车来车往,流水依旧浩荡如斯,但已不见了当年的摆渡人。
此刻,正值夕阳西下。橘黄色的残照里,渡口空空如也,高台上荒草丛生。那一座小小的窝棚,早已淹没在野蒿里。再寻那一条船,发现它底部朝天,倒扣在河畔的蓼花丛里,仿佛一块鱼骨化石。
流水光阴总无情。久久地,伫立在古渡残照中,我不知道自己在等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