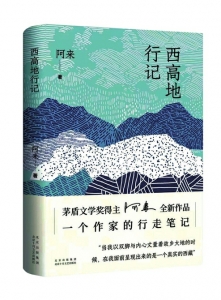融合“风物书写”与“博物学”
众专家研讨阿来“大横断写作”
研讨会现场。
《西高地行记》
熟悉阿来文学世界的人都知道,阿来的写作总体有两个大的方向:虚构与非虚构。在虚构方向,他写出《尘埃落定》《云中记》等口碑甚高的优秀小说。在非虚构的方向,他出版过《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等散文随笔作品,也深受读者喜爱。当然这两个方向也有交汇之处,非虚构、大自然意识也渗透到阿来的虚构小说创作领域。比如在阿来的“自然三部曲”(《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中,就将小说虚构艺术与物候自然书写进行了很好的融合。
今年6月,阿来的最新散文作品集《西高地行记》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备受瞩目。11月28日上午,由四川省作协主办,四川省作协创作研究室、《阿来研究》集刊承办的“阿来《西高地行记》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写作没有离开“大横断”空间
研讨会上,在作家杨献平的主持下,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阿来研究》集刊主编陈思广,绵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教授冯源,中南民族大学文新学院教授李长中,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唐小林,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谭光辉,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作家蒋蓝,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高树博,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博士袁佳慧、朱意等人,围绕《西高地行记》,研讨了阿来的散文、游记书写的特色、意义和价值。四川省作协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李铁出席本次研讨会。
袁佳慧博士特别从“博物学”、生态与文学的综合视角分析了阿来在《西高地行记》的自然书写。朱意博士则从听觉、视觉等多重叙事角度赏析了这部作品。作家蒋蓝则特别分析阿来的游记写作属于跨文体、跨学科的“大横断写作”。众人一致认为,阿来的散文写作,是“言之有物”的写作。有评论家认为,阿来写的不只是游记散文,还是一部民族志。
阿来常年在横断山脉以及更远的大地上行走探索,并与阅读互相映照,这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蒋蓝特别指出,阿来的写作可以归纳为“‘大横断’写作”,“在我看来,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阿来的写作都没有离开‘大横断’这个地理空间。他的文学世界基本是在这个地理空间里腾挪。”
作为有着丰富散文、非虚构创作经验的作家,蒋蓝特别提到,是不是跨学科、跨文体,是区分非虚构与散文的重要标准。在蒋蓝看来,将中国传统笔记文学中的风物写作和西方式的博物学视野进行融合,是阿来写作尤其是非虚构写作中非常重要的文学方法。
恢复散文对现实的表达活力
“行走不光是为了看见,而且是有所思考感受。有一天我想能不能把自己在大地上的行走和思考写成一本书,于是就有了这本《西高地行记》。”阿来说。《西高地行记》收录了《故乡春天记》《嘉绒记》《贡嘎山记》《平武记》《玉树记》《果洛记》《山南记》《武威记》《丽江记》9篇长散文。这本书最早的篇目,大概写于十五年前,最近的篇目写于两年前。
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主角,在会议的最后环节,阿来从《嘉绒记》《平武记》《武威记》《丽江记》几篇文章出发,分享自己这些年来到处行走的宗旨,“我对大横断区的关注,一开始主要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生物多样性,然后是文化多样性。”阿来透露,自己已经写了《敦煌记》,目前尚未收入书中,《西高地行记》出新版的时候可能会加进去。
阿来也谈到散文这种文体,“打开《古文观止》,我们会发现,里面收入的散文很多都不是纯文学,而是应用文,比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今天如何恢复散文的活力,恢复散文对现实的强大叙述能力,这是值得努力的。我愿意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
在这些散文中,阿来用他优美的文笔和深邃的思考,表达他对大自然山川河流的充沛感情。比如他这么写黄河:“青藏高原上的黄河,就这么萦回,这么涌流,就像这片高原上的人群,那样安详,听天由命,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就像我现在,站在四合的暮色中,看黄河映射的天光渐渐暗淡,只是将其当作一股源源不绝的情感,把我充满。而黄河在草原上百转千回,唯一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水流越发丰沛。”
阿来到访过诸多峡谷里的河流,同时他在书中承认,其实真正到达源头的屈指可数。这是因为,所有的源头都非常难以抵达。他写道:“这每一条河流,无论我多么熟悉它们中下游的牧场、村落、城镇,多么熟悉一条河流与另一条河流相逢汇合的地方,但它们的上游,那些远离人烟的雪山丛中的发源地,总是因为险峻而难以抵达。”
阿来对自然文学情有独钟,圈内有名。他多年来一直比较关注文学作品之外的自然环境、植物学、动物学的书。他热爱到户外徒步、摄影,有着强大的自然知识系统。他在青藏高原拍摄植物,至今已积累几万张照片。阿来曾提到,当下的文学,多是聚焦人与人的关系,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的丰富,却较少触及。就算是触及,也不是专门关照自然本身,而是将自然作为一种意象的投射物,“它不再是自然物,变成了一种寄予我们情感的事物。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词——象征。荷花是什么?从《爱莲说》开始就有这样的意象,它变成一种象征事物,梅花、兰花等也有其意义。当赋予植物象征意义的时候,其自然意义就慢慢萎缩了,作家只书写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的意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姜孟欣 四川省作协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