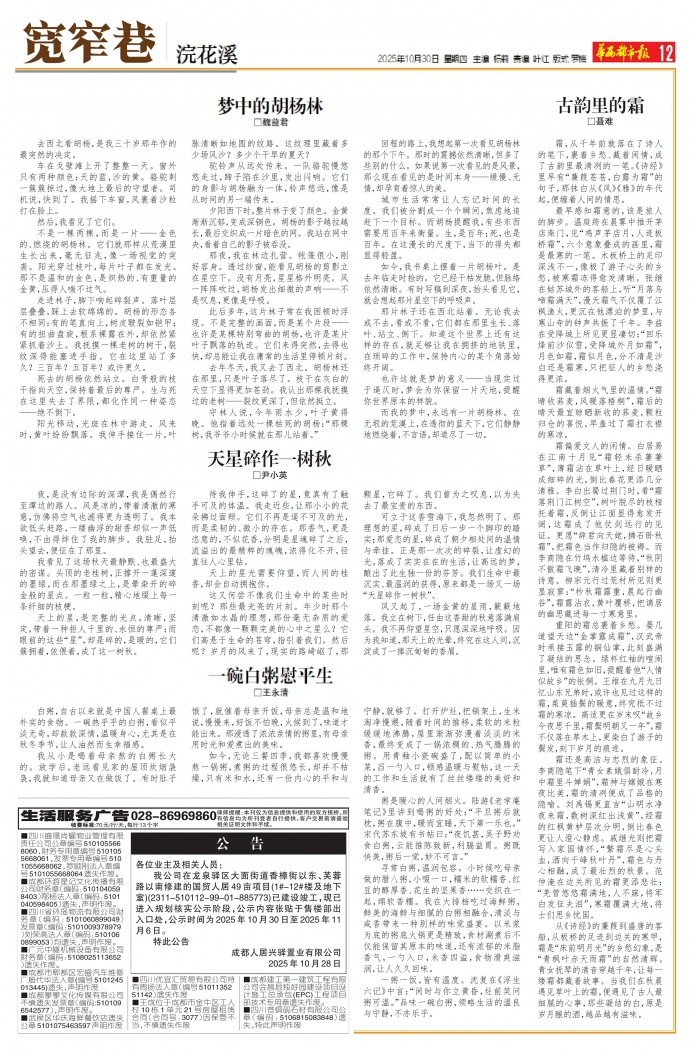梦中的胡杨林
□魏益君
去西北看胡杨,是我三十岁那年作的最突然的决定。
车在戈壁滩上开了整整一天。窗外只有两种颜色:天的蓝,沙的黄。骆驼刺一簇簇掠过,像大地上最后的守望者。司机说,快到了。我摇下车窗,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
然后,我看见了它们。不是一棵两棵,而是一片——金色的、燃烧的胡杨林。它们就那样从荒漠里生长出来,毫无征兆,像一场视觉的突袭。阳光穿过枝叶,每片叶子都在发光。那不是温和的金色,是炽热的、有重量的金黄,压得人喘不过气。
走进林子,脚下响起碎裂声。落叶层层叠叠,踩上去软绵绵的。胡杨的形态各不相同:有的笔直向上,树皮皲裂如铠甲;有的扭曲盘旋,根系裸露在外,却依然紧紧抓着沙土。我抚摸一棵老树的树干,裂纹深得能塞进手指。它在这里站了多久?三百年?五百年?或许更久。
死去的胡杨依然站立。白骨般的枝干指向天空,保持着最后的尊严。生与死在这里失去了界限,都化作同一种姿态——绝不倒下。
阳光移动,光斑在林中游走。风来时,黄叶纷纷飘落。我伸手接住一片,叶脉清晰如地图的纹路。这纹理里藏着多少场风沙?多少个干旱的夏天?
驼铃声从远处传来。一队骆驼慢悠悠走过,蹄子陷在沙里,发出闷响。它们的身影与胡杨融为一体,铃声悠远,像是从时间的另一端传来。
夕阳西下时,整片林子变了颜色。金黄渐渐沉郁,变成深铜色。胡杨的影子越拉越长,最后交织成一片暗色的网。我站在网中央,看着自己的影子被吞没。
那夜,我在林边扎营。帐篷很小,刚好容身。透过纱窗,能看见胡杨的剪影立在星空下。没有月亮,星星格外明亮。风一阵阵吹过,胡杨发出细微的声响——不是叹息,更像是呼吸。
此后多年,这片林子常在我困顿时浮现。不是完整的画面,而是某个片段——也许是某棵特别弯曲的胡杨,也许是某片叶子飘落的轨迹。它们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却总能让我在庸常的生活里停顿片刻。
去年冬天,我又去了西北。胡杨林还在那里,只是叶子落尽了。枝干在灰白的天空下显得更加苍劲。我认出那棵我抚摸过的老树——裂纹更深了,但依然挺立。
守林人说,今年雨水少,叶子黄得晚。他指着远处一棵枯死的胡杨:“那棵树,我爷爷小时候就在那儿站着。”
回程的路上,我想起第一次看见胡杨林的那个下午。那时的震撼依然清晰,但多了些别的什么。如果说第一次看见的是风景,那么现在看见的是时间本身——缓慢、无情,却孕育着惊人的美。
城市生活常常让人忘记时间的长度。我们被分割成一个个瞬间,焦虑地追赶下一个目标。而胡杨提醒我,有些东西需要用百年来衡量。生,是百年;死,也是百年。在这漫长的尺度下,当下的得失都显得轻盈。
如今,我书桌上摆着一片胡杨叶。是去年临走时捡的。它已经干枯发脆,但脉络依然清晰。有时写稿到深夜,抬头看见它,就会想起那片星空下的呼吸声。
那片林子还在西北站着。无论我去或不去,看或不看,它们都在那里生长、落叶、站立、倒下。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存在,就足够让我在拥挤的地铁里,在琐碎的工作中,保持内心的某个角落始终开阔。
也许这就是梦的意义——当现实过于逼仄时,梦会为你保留一片天地,提醒你世界原本的样貌。
而我的梦中,永远有一片胡杨林。在无垠的荒漠上,在透彻的蓝天下,它们静静地燃烧着,不言语,却道尽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