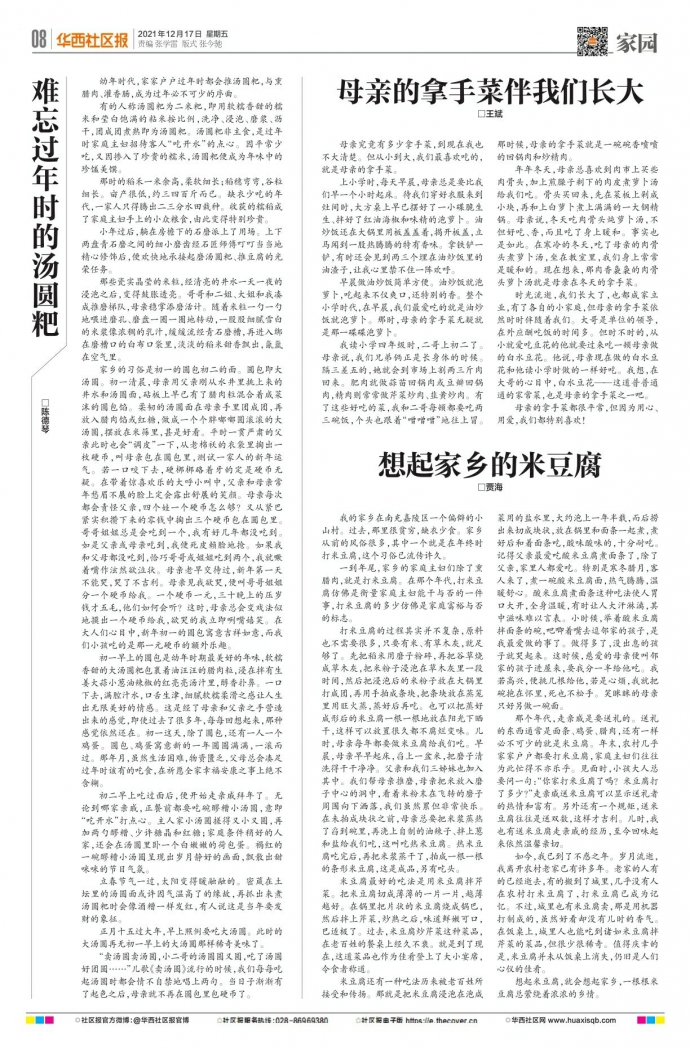难忘过年时的汤圆粑
□陈德琴
幼年时代,家家户户过年时都会推汤圆粑,与熏腊肉、灌香肠,成为过年必不可少的序曲。
有的人称汤圆粑为二米粑,即用软糯香甜的糯米和莹白饱满的粘米按比例,洗净、浸泡、磨浆、沥干,团成团煮熟即为汤圆粑。汤圆粑非主食,是过年时家庭主妇招待客人“吃开水”的点心。因平常少吃,又因掺入了珍贵的糯米,汤圆粑便成为年味中的珍馐美馔。
那时的稻禾一米余高,柔软细长;稻穗弯弯,谷粒细长。亩产很低,约三四百斤而已。缺衣少吃的年代,一家人只得腾出二三分水田栽种。收获的糯稻成了家庭主妇手上的小众粮食,由此变得特别珍贵。
小年过后,躺在房檐下的石磨派上了用场。上下两盘青石磨之间的细小磨齿经石匠师傅叮叮当当地精心修饰后,便欢快地承接起磨汤圆粑、推豆腐的光荣任务。
那些瓷实晶莹的米粒,经清亮的井水一天一夜的浸泡之后,变得鼓胀透亮。哥哥和二姐、大姐和我凑成推磨梯队,母亲稳掌添磨活计。随着米粒一勺一勺地喂进磨孔、磨盘一圈一圈地转动,一股股细腻雪白的米浆像浓稠的乳汁,缓缓流经青石磨槽,再进入绑在磨槽口的白布口袋里,淡淡的稻米甜香飘出,氤氲在空气里。
家乡的习俗是初一的圆包初二的面。圆包即大汤圆。初一清晨,母亲用父亲刚从水井里挑上来的井水和汤圆面,砧板上早已有了腊肉粒混合着咸菜沫的圆包馅。柔韧的汤圆面在母亲手里团成团,再放入腊肉馅或红糖,做成一个个胖嘟嘟圆滚滚的大汤圆,摆放在米筛里,甚是好看。平时一贯严肃的父亲此时也会“调皮”一下,从老棉袄的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叫母亲包在圆包里,测试一家人的新年运气。若一口咬下去,硬梆梆硌着牙的定是硬币无疑。在带着惊喜欢乐的大呼小叫中,父亲和母亲常年愁眉不展的脸上定会露出舒展的笑颜。母亲每次都会责怪父亲,四个娃一个硬币怎么够?又从紧巴紧实积攒下来的零钱中掏出三个硬币包在圆包里。哥哥姐姐总是会吃到一个,我有好几年都没吃到。如是父亲或母亲吃到,我便死皮赖脸地抢。如果我和父母都没吃到,恰巧哥哥或姐姐吃到两个,我就噘着嘴作泫然欲泣状。母亲老早交待过,新年第一天不能哭,哭了不吉利。母亲见我欲哭,便叫哥哥姐姐分一个硬币给我。一个硬币一元,三十晚上的压岁钱才五毛,他们如何会听?这时,母亲总会变戏法似地摸出一个硬币给我,欲哭的我立即咧嘴嬉笑。在大人们心目中,新年初一的圆包寓意吉祥如意,而我们小孩吃的是那一元硬币的额外乐趣。
初一早上的圆包是幼年时期最美好的年味,软糯香甜的大汤圆粑包裹着油汪汪的腊肉粒,浸在拌有生姜大蒜小葱油辣椒的红亮亮汤汁里,醇香扑鼻。一口下去,满腔汁水,口舌生津,细腻软糯柔滑之感让人生出无限美好的情感。这是经了母亲和父亲之手营造出来的感觉,即使过去了很多年,每每回想起来,那种感觉依然还在。初一这天,除了圆包,还有一人一个鸡蛋。圆包、鸡蛋寓意新的一年圆圆满满,一滚而过。那年月,虽然生活困难,物资匮乏,父母总会凑足过年时该有的吃食,在祈愿全家幸福安康之事上绝不含糊。
初二早上吃过面后,便开始走亲戚拜年了。无论到哪家亲戚,正餐前都要吃碗醪糟小汤圆,意即“吃开水”打点心。主人家小汤圆搓得又小又圆,再加两勺醪糟、少许糖晶和红糖;家庭条件稍好的人家,还会在汤圆里卧一个白嫩嫩的荷包蛋。褐红的一碗醪糟小汤圆呈现出岁月静好的画面,飘散出甜咪咪的节日气氛。
立春节气一过,太阳变得暖融融的。密蔵在土坛里的汤圆面或许因气温高了的缘故,再抓出来煮汤圆粑时会像酒糟一样发红,有人说这是当年要发财的象征。
正月十五过大年,早上照例要吃大汤圆。此时的大汤圆再无初一早上的大汤圆那样稀奇美味了。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圆又圆,吃了汤圆好团圆……”儿歌《卖汤圆》流行的时候,我们每每吃起汤圆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唱上两句。当日子渐渐有了起色之后,母亲就不再在圆包里包硬币了。